正常是⋯⋯像愛人和被愛那樣 —— 莎拉・魯尼《正常人》
那等待的時間,代表的是尊重、放手與自由。而「被動」則是這試煉、教養的外在模式,出之以謹慎,成之以壓抑,期許無害無傷於人,也就能勉強維持已身自我——這最後、最私密,也最脆弱的,容身之處的微小自主與完整。
您的數位閱讀序號權限期間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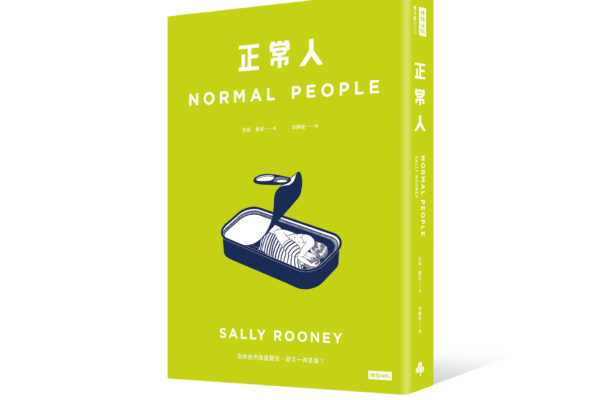
那等待的時間,代表的是尊重、放手與自由。而「被動」則是這試煉、教養的外在模式,出之以謹慎,成之以壓抑,期許無害無傷於人,也就能勉強維持已身自我——這最後、最私密,也最脆弱的,容身之處的微小自主與完整。

「犯罪實錄」可以視為「犯罪小說」的鏡像:前者為非虛構紀實,需要倚賴縝密的資料蒐集與多人訪談對真實事件提出觀點並加以剖析;後者則為虛構杜撰,線索安排及情節設計全憑創作者規劃構思,但兩者皆以現實世界的犯罪與查案活動為基礎來進行創作。

用一個更白話的講法來說:過去的同志文學,讓人看見生活在暗處的同志,其感情、壓抑、思想與生態,那麼當同志不再需要透過文學(或其他方式)而能直接被大眾與社會看見,同志文學還要、還能寫什麼?如果同志和一般人一樣,那特別標舉「同志文學」又能產生什麼意義?

這並不是一個屢屢在鬼門關前徘徊,以書寫戰勝死亡的故事。或許我們更應該視為一次一次的失敗,無數的死亡。每一次書寫下來,都見證複數的死亡,包括作者的。抑或,每一次書寫,皆代表一次的死亡,與道別,當然包括對作者自己。

近期推理小說家張國立與臥斧,分別以「一道料理」為主題各自推出新作,與《週刊編集》一起聊聊,想像的起點如何隱藏在西門町巷弄裡、在城市大樓裡,以及飲食嗅覺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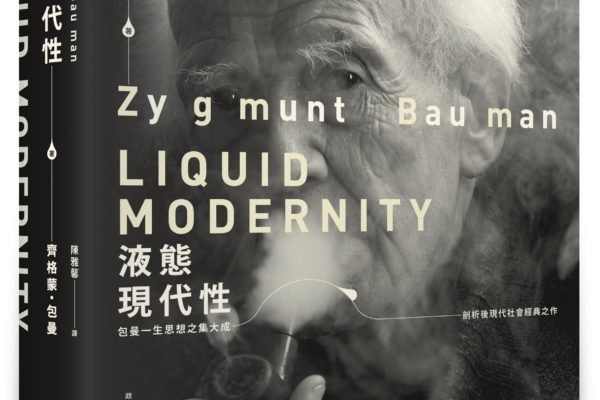
社會學理論的發展,譬如諸位大師與流派,許多時候倚賴某種使用隱喻的能力。比如孔德的生物學隱喻、馬克思主義的建築比喻(上層結構/下層結構)、遊戲或競技比喻(例如布赫迪厄的「場域」)、語言學比喻(結構主義)、文本比喻(詮釋人類學)等等。包曼的策略依此訂立,並令人稍微訝異的,不是新穎獨特,反倒是相當古典且有效。在閱讀與思考時,可以注意其意圖,不僅僅在於開創,包曼的視野裡,延續社會學理論可能擺在優先。或濫情一點說,讀起《現代液態性》的「新」,並不是某些稍微激進的後現代主義(雖然可能在這本書之前,這類的取向已是強弩之末了),至少對待現代性方面,採取較溫情的調子。然而,若包曼真如此想,抓著現代性主題的延續(而非斷裂),非得小心翼翼處理的,就是差異性的問題,因為即使再陌生於理論史的讀者,也不可能認為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理論大家所談的現代,與我們的當代會是相同的。所以讀者必然的問題也可以轉化成:「液態」一詞要怎樣的有效,使得當代這「社會」一詞都岌岌可危的狀況下,仍可以保持「現代性」的觀念有效?

是誰讓雨變苦的呢?這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人類,卻同時可以有兩層意涵,第一層是反省人類破壞自然、使雨變苦的種種作為,第二層,亦即「誰來定義怎樣的狀態是苦」,則是更深入本質、更根本地察覺詞語背後人類中心的價值預設與區判——《苦雨之地》開創出的自然書寫反思空間,也就在於此。

一九六八年發生了很多很多事:暗殺、占領、抗議、死亡、文革、黑權、「白色專輯」(White Album),或者,「想像力奪權」。
世界在那之後不太一樣了。
除了音樂、電影、藝術,在新聞寫作和文學領域也在那一年出現新的力量,人們稱之為「新新聞」(New journalism)。

什麼樣的心境投射在詩裡會引起較多迴響?不僅是年輕世代的一種特定寂寞與哀傷,更還有那些說不出來的狀態。近期出版新作《失物風景》的陳夏民,擁有出版經營者、圖書編輯,與閱讀節目主持人等多種身分,在訪談中透過兩首〈除魅的家屋〉、〈前中年書〉這兩首詩與書中的自己呼應,傳達邁向四十歲、前中年的心得。
「它們傳達一種悶的感覺,活在世界,想說但說不出來的狀態。最明顯的,像是〈除魅的家屋〉裡這句:『為了隱瞞其中的陰溼,故意忘記開鎖的方式』。」陳夏民說。他進一步解釋,人到了一個年紀之後會變成這個狀態:誤以為自己長成了自己的樣子,理想中的狀態會像是一種酷刑把自己限制了——你不是他,因為你本來就不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