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不僅是孤獨者的救贖,更是孤獨的證明—— 勒・克萊喬《碧娜,首爾天空下》
唯死亡真實,正好反證生命充滿虛假。但故事的虛構性未必因此折損,反而增加了感性色彩。由此省察,故事或謊言,無非種種願望;碧娜為莎樂美所說的每個故事:鴿子們、貓「旅行者」、菜鳥謀殺者、歌手娜比、護士河娜與「她的娜奧美」、兩條龍⋯⋯乃至於她自己虛實難辨的故事都是。而至為關鍵的,不在願望實現與否,更繫於對願望憧憬的心情——於是可以試著對(不堪的、難以忍受的)生活、命運、遺憾、他者,再忍受一下,努力一下,直到改變的契機出現。也呼應那句關於邂逅的首爾諺語,「總有一天,會在首爾天空下重逢。」


立體300dpi-600x40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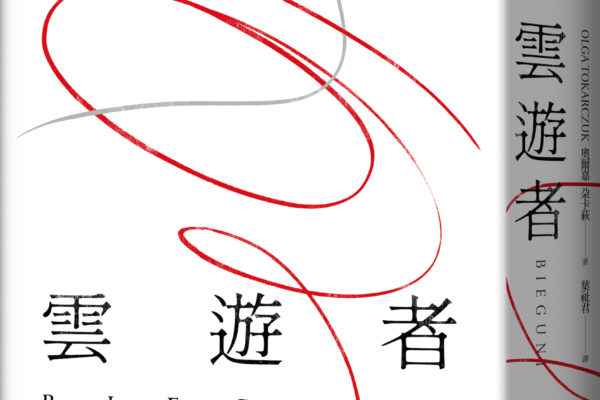


-ISBN9789570845990-600x40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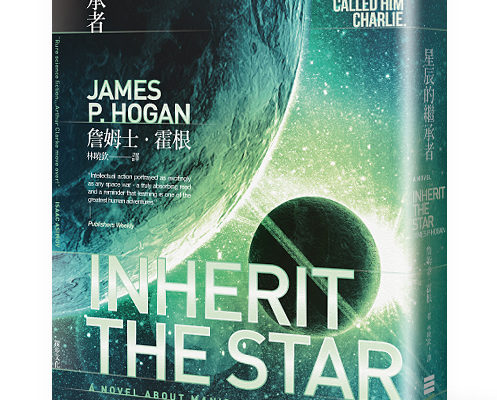
-1-600x400.jpg)
性意思史立體書封300-600x4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