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們讚許「台灣擁有全世界最好的 XR 創作環境」——周東彥的旅法十日談
新媒體科技未來的發展,似乎也環繞在人與人的關係經營上。周東彥相信科技、藝術與「寂寞經濟」的連結,因寂寞而創生出來的需求,能否透過藝術文化得到緩解?倘若連審美的經驗都能夠不斷地流動,那麼科技還能夠如何縮短人的距離,使得「沉浸」的感受擴大至身旁的人呢?
您的數位閱讀序號權限期間為

新媒體科技未來的發展,似乎也環繞在人與人的關係經營上。周東彥相信科技、藝術與「寂寞經濟」的連結,因寂寞而創生出來的需求,能否透過藝術文化得到緩解?倘若連審美的經驗都能夠不斷地流動,那麼科技還能夠如何縮短人的距離,使得「沉浸」的感受擴大至身旁的人呢?

我們常常把教育想像成「空瓶裝水」的過程:學生的腦袋就是空的,而老師則是裝水者,達到「醍醐灌頂」的效果。在這個模型下,老師和學生的差異只在老師有更多的水——知道的更多、更有知識。但顯然,遇到 ChatGPT,這個模型很快就崩潰了。

先來看比較負面的觀點。當我們說 ChatGPT 勢必或即將取代人類,這通常意味著我們認為 ChatGPT 能夠做到只有人類才能夠做到的事情——是哪些事情呢?人類會吃喝拉撒睡,其他動物也會,所以不是這類生理機能。人類會思考、有語言,團體合作和社會結構由此而生,這才是其他動物多半無法也不曾擁有的。

韓國企業 Kakao 娛樂希望能更進一步,因此與手機遊戲公司「網石遊戲」合作,打造了一個名為 Mave 的 K-pop 女團,這個女團僅存在於網路世界,四名虛擬成員與世界各地的真實粉絲互動。Kakao 還推出了元宇宙選秀節目《少女 RE:VERSE》,此節目2月在串流平台上推出第一集,三天觀看次數就突破了100萬。

開發僅僅幾個月,DALL-E 2、Midjourney 和 Stable Diffusion 等軟體就已經改變了電影製作人、室內設計師和其他專業創意工作者的工作方式。

技術不只依靠科學理性,生產效率也不是唯一,研究者該探究和思考的於是轉變為:技術是在什麼樣的情境脈絡下成為眼前所見的樣態。這意味著,雖然哲學事業有九成都是抽象化的工作,但技術哲學不見得也必須如此。技術哲學可以從極度抽象的、大寫的 Technology 轉向小寫的、複數的 technologies。

根據許許多多的後續追蹤,不論是不同國家的跨地域研究,或長達十年的跨時間研究,都顯示人們在接受環境教育之前與之後的行為模式差異不大。換句話說,環境行為與環境教育的相關程度很低——人們行事是否環保和有無接受環境教育沒什麼關係。為什麼會這樣?

CC 注意到疫情期間的 VR 用戶數量大幅增加。對於那些待在家裡、有錢有閒的人來說,VR 似乎是一項有吸引力的科技工具、一種擺脫現實世界的平庸和恐怖的簡單方法,並在不冒著吸入有害病毒之風險的情況下,與他人交流。如果還能結識新朋友、與他們談情說愛,甚至來場異國情調的約會?再好不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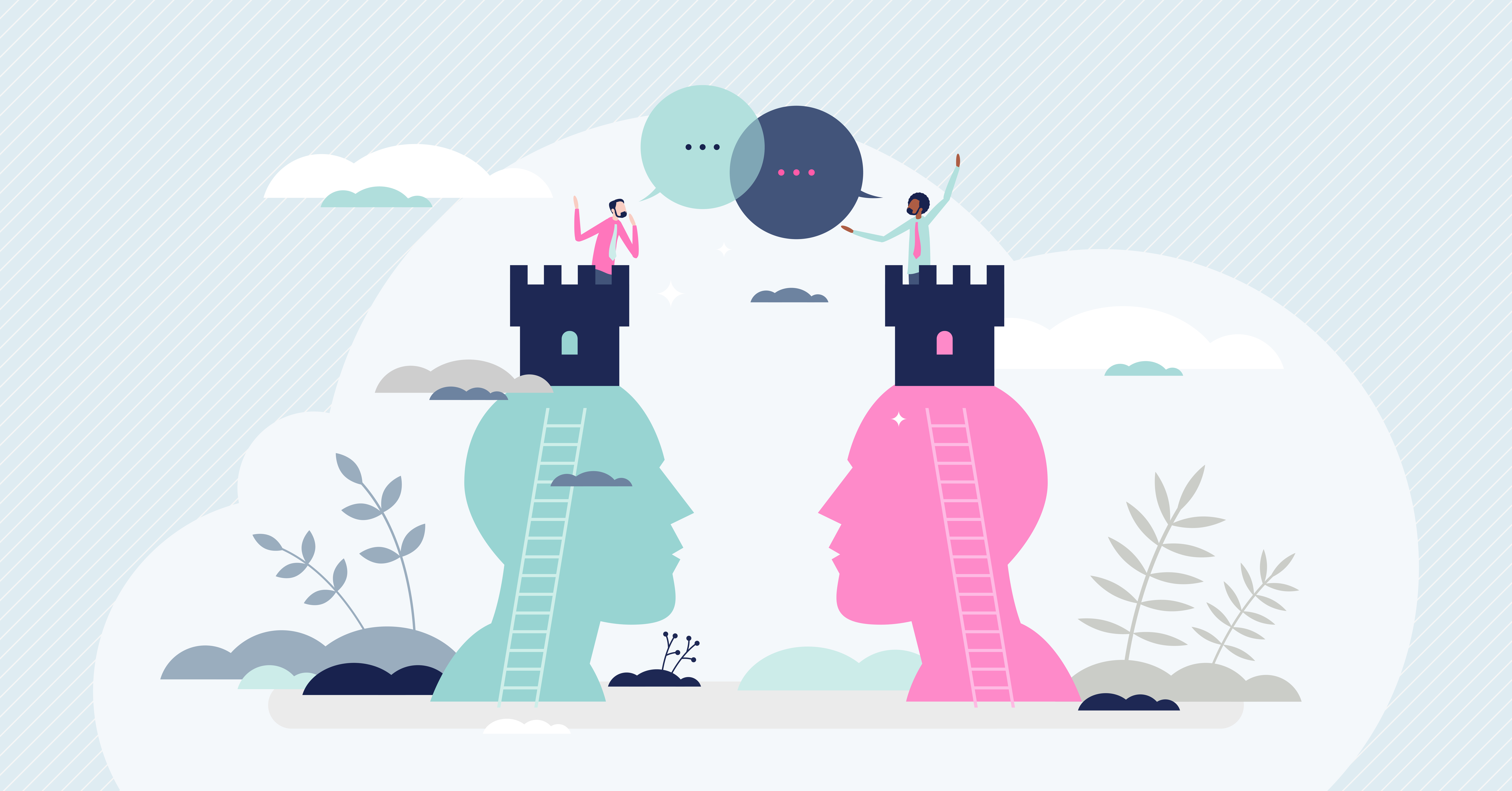
從演化倫理學的角度來看,某個價值能被看重、被當成是社會上的標準,通常是因為那個價值除了有利於個人生存之外,往往也有利於群體生存。某個價值之所以有價值,在於攜帶該價值的文化存活得夠久,久到讓這個價值被肯定和推崇。

抱著孩子唱歌可以一次達到建立連結和情感的目的,它涉及動覺、聽覺、視覺,並已被證實可以改善媽媽的健康和幫助兒童發育。從醫療層面來看,好處是顯而易見的:搖籃曲對早產兒的心臟和呼吸功能有正向影響,它們降低了焦慮的照護者的心跳,使其成為一種近乎零成本的煩惱解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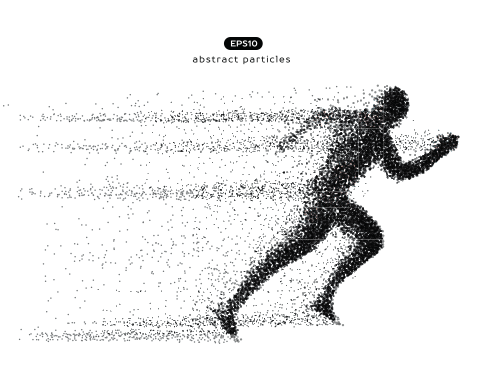
尼采認為,人類總是被要求成為某個特定樣貌,以便符合某些特定標準。人類一直囿於某個價值體系,被迫跟隨當時什麼是好、什麼是壞的定義,而這樣的價值體系,無疑是某種壓迫性的權力彰顯。因此,人類應該做的,不是去遵守當代認定的價值,而是去質疑、推翻、甚至超越,如此才能成為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