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生命強震的群像——讀《JR上野站公園口》
其實,仔細一想,陷入自責的主角不斷回憶兒子死亡的瞬間,某部分的潛意識自然想拒絕收聽。對他來說,東北 311 地震後的蕭條使他必須離鄉工作,雖然辛苦卻還堪忍。最難以忍受的是兒子之死,那有如大地震般在他生命中掀起巨濤
您的數位閱讀序號權限期間為

其實,仔細一想,陷入自責的主角不斷回憶兒子死亡的瞬間,某部分的潛意識自然想拒絕收聽。對他來說,東北 311 地震後的蕭條使他必須離鄉工作,雖然辛苦卻還堪忍。最難以忍受的是兒子之死,那有如大地震般在他生命中掀起巨濤

這座彼岸花盛開之島上居住的並非開天闢地以來的化外之民,而是從日本、台灣出逃的流亡者。島嶼上的多語系與先來後到的不同族裔有關,而之所以女語才能傳承本島歷史、女性作為領導人乃是對錯誤歷史的補償。歷史沒有偶然,不論以什麼理由來到此島的人,都見證了鮮血遍地的戰爭。先來者驅除後來者,兩相爭戰,後來者又拒斥霸凌了島內更弱勢的人,如次循環。這樣的歷史除了重複傷痛,還能帶來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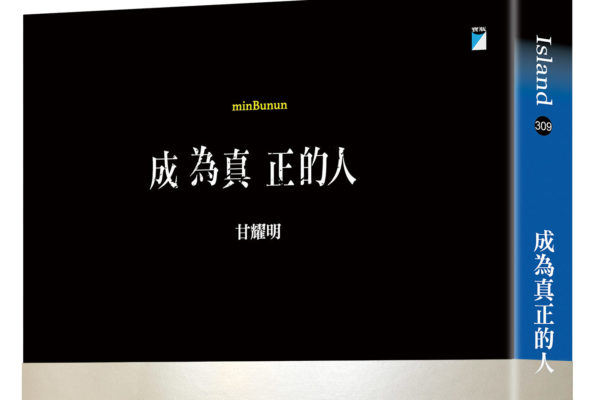
台灣,歷經不同政權,融合多樣族裔,這座年輕島嶼在輪番暴力下,最底層顯透而出的特質,或許是消融與和解。哈魯牧特欲與美軍生還者湯瑪士之間辯證出是非對錯的場景在狂風驟雨襲擊下,仇怨角力到最後何以泯滅?湯瑪士選擇為自己注射過量嗎啡。他清晰的澄澈自知,此行絕無生還,在凍死之前主動殞滅肉身,對哈魯牧特來說,極有可能會成為一種道成的啟示與懺悔。

《不冷的紅茶》是小川洋子轉變前的小說集,買到此小說集,書內頁點點泛黃,如幾個月未洗的抽油煙機,像紅茶戚風蛋糕裡的點點茶葉。打開內頁,我便知道轉變在哪,早期的小川洋子喜歡說死亡。

無論科技再萬能,亦非無所不能。人類注定擁有的孤寂、脆弱與短暫,哪怕是運用技術頑抗,完整與不朽都離人類萬分遙遠。不過,正是這份「可一不可再」的痛切讓「人不能踏過同一條河兩次」不光作為名言,而顯然晉升為普世經驗。金草葉《如果我們無法以光速前進》鍛造的時間空間曲度再大,未來世界之難以測料,我們都能感受到某種共通性——生命本身即有奇點。

我們討厭的人,為什麼討厭呢?我們能說好幾個厭惡的理由,卻常常說不出我們在意的點。離別是消失,辦公桌上不見的名牌、共用衣櫃裡頭少了一個衣架,都讓讀者與裡頭的角色頓了幾秒。那幾秒是尋找共同感受的時間,我想起少年時期轉學離開的同學,那個討人厭的轉走了,下課少了些喧鬧。

自大學起即持續自費出版插畫作品集的高妍,在台日獨立出版界早已為人熟知。2018年,高妍將自己愛上日本搖滾巨匠細野晴臣的經歷,繪製成32頁的短篇漫畫作品《綠之歌》自費出版。這部作品輾轉流傳至日本,被細野晴臣曾組成的樂團 HAPPY END 鼓手、作詞人松本隆發現,進而轉達給細野晴臣本人,書中的真摯情感,也因而傳達到了他手中。

《鹹海敘事曲》裡的所有人物,乃至德國海軍軍官,旅行在定位模糊的群島間,彷彿在葛羅斯維諾家族的系譜分支上遊走,驚愕連連,而不曾觸及目的地。他們與地理上的真相擦身時,渾然不覺。

雨果.帕特對歷史和地理的知識豐富,畫功深厚,筆觸靈動,細節考究,線條從簡。即使過了半個世紀,《科多.馬提斯》仍是不可取代的經典,美妙的黑白畫面、復古的神韻,筆下的小島和民族風情,細緻得有如考古。

2003 年,世界聞名的法國博物館羅浮宮開始了「BD Louvre」計畫(BD = Bande dessinée,意為法國漫畫,BD Louvre 譯為「當羅浮宮遇見漫畫」)。這計畫是邀請漫畫家到館自由創作,除可在閉館後自由走動,更可深入一些平常不開放的展間,創作的唯一限制就是「羅浮宮」三字。近20年來,羅浮宮與漫畫家共同創作漫畫,介紹了更多羅浮宮的館藏與神祕的空間。

《再見,烏斯曼》詳實生動地講述了抵達義大利的非洲人面臨何等命運——他們如何生活、如何工作,以及最重要的是,如何抵抗。正如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在1930年代末與貧困的採摘工人一起往西穿越塵爆區後,將自己發給《舊金山新聞》(San Francisco News)的快電轉化為引人入勝的大作《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白曉紅也汲取自己在第一線與非洲移工相處的生活經驗,勾勒出她筆下這些義大利「必要棄兒」令人痛苦的生活全貌。
獨裁者的廚師-立體書封有書腰300dpi-600x400.jpeg)
在〈台灣版作者序〉中自況本書:內容貌似談論食物,實際上又是本關於自由的書。乍看之下或許有些困惑,但隨著經歷四年書寫、橫跨四大洲,踏查與訪談近現代最讓人聞之色變的五大暴力政權獨裁者 —— 然而並非直訪獨裁者本人,而是他們的貼身專屬大廚,透過飲食開展一幕幕過往難以窺見的獨裁者與其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