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們,安嗎?
條仔是捲毛忠心耿耿的小弟,捲毛是照顧他的大哥,兩人合體時自帶氣場,形成一道外人攻不破的牆。他們的存在就像一種展示,展示給老師看,給月經來潮的女生看,給回家看色情漫畫打手槍的男生看。每天似乎都不用上課、不用升降旗、不用掃地倒垃圾,甚至不用吃飯。
您的數位閱讀序號權限期間為

條仔是捲毛忠心耿耿的小弟,捲毛是照顧他的大哥,兩人合體時自帶氣場,形成一道外人攻不破的牆。他們的存在就像一種展示,展示給老師看,給月經來潮的女生看,給回家看色情漫畫打手槍的男生看。每天似乎都不用上課、不用升降旗、不用掃地倒垃圾,甚至不用吃飯。

水塔依偎在山屋旁邊,是一個更小的三角形,空曠的高海拔冰冷如月球,出水口上覆了一層霜,忽然在我眼前活了起來,蔓延到腳下的土丘、山屋旁的石徑,最後蔓延到遍布在整片山脊上數不盡的刺柏。我提著喝飽的水袋起身,頭燈的光束掃過周遭的喬木林,亮晃晃的像一大片銀色聖誕樹,頂著一月的寒冰。

碎開的心終究會被時間癒合,職業運動雖然目的是求勝,失敗同樣可以定義一個人。不只是大滿貫總數,曾經費德勒創下的所有不可思議的紀錄,已經一項一項被納與喬給超越,但每個費迷都有一本珍藏的費德勒編年史,裡面記載了自己的生命和那個風度翩翩的瑞士人的交疊,以及記憶中的想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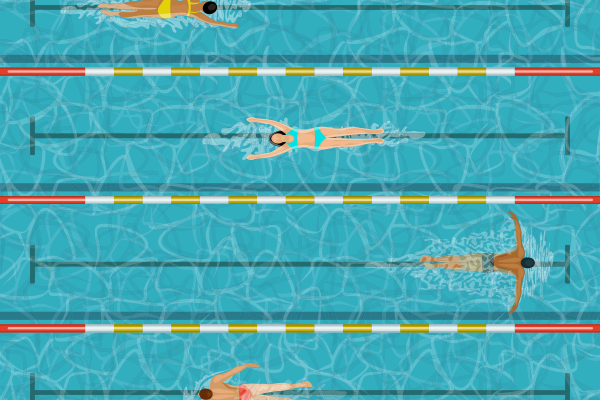
如同人生多數需要練習之事,勤勉會創造初期的學習高峰,帶來成就感。狀態好的時候,我被浮力穩穩接住,傾聽著安靜的聲浪,身體在水中喜悅地舒張開來,進到一種完全當下的境界——沒有過去與未來,只有這個奮力划水的此刻。

凹凸的岩稜上無植被可供遮蔭,暑熱中大夥冒著汗,帶著敬畏的心情在高峰間縱走著,在空中排隊等紅燈轉綠,好越過下一個山頭。總算攻上凱蘭特昆山,往東方望去,隔著一座黑森林可見三六九山莊的影蹤,正路旁岔開一條直達山莊的捷徑,意味著只要腳程夠快,今天就能返家。

林道通常悶在濕熱的中海拔地帶,走起來往往滿身大汗,「風景」多半被茂密的雜林遮擋住了,既無複雜地形讓人留心通過,也無開闊景緻使人忘卻疲勞。聖稜線的名號太響亮——有人說,它是台灣人一生要走過一次的路線,此行的領隊與隊員加起來共19人。我很久沒參加這麼熱鬧的隊伍了,其中有一同經歷過多次深山探險的老戰友,有初次相遇的新夥伴,還有三位「完百」人士。

這年張雨生19歲,戴著眼鏡,頭髮理得很整齊,一付愛國青年的模樣。他穿過狹長的走廊,一間間探頭進去,靦腆地和未來的同學打招呼。每扇門後面都開著收音機,每台收音機都播著〈明天會更好〉,那首當年響遍每個角落的公益歌曲。三年後,他的〈我的未來不是夢〉也會風靡每一戶人家,成為台灣解嚴後的主題曲。

離開的那天,車子終於開過墾丁大街,觀光客在攤商前排著隊,要買「風景區」才有的那種一整顆椰子汁。一行人在鵝鑾鼻燈塔下拍了張合照,幾個小孩身上都和我們年輕時一樣,飄著鹽的氣味。海風徐徐吹來,吹過青春的足跡,我們被別人難以明瞭的經歷聯繫著。

早在三鐵共構,結構開始複雜化之前,從前它叫「台北火車站」,日治時代則叫「台北驛」。流轉的歲月凝視著現代化的進程,鐵軌和平交道在城市的地景中消失,火車駛過的轟隆轟隆也在聲景中去除。列車愈鑽愈深,月台由平行變成立體。

那是很細微的一種聲音,好像有電磁波在耳道裡流動,發出「嘶嘶」的聲響。初期我感覺它似乎有週期,會因為前一天的睡眠時間、疲勞程度和壓力大小(這裡指心理的壓力)而受影響,我也試過連續幾天都不聽音樂,減少耳朵的用量。

靜謐的晨間,好長一段路山谷裡只有我們這輛車,偶爾瞥見猴群在大理岩間活動。車在山洞裡穿行,如悠遊於神的兩指間,一側是暗藍色的即將被太陽照亮的深潭,一側是險峻的峭壁。行過燕子口和九曲洞,路中央開始有滑下來的落石,K 熟練地開著山路,轉彎時整個人好像攀附在方向盤上,用她常掛在岩壁間的雙手雙腳,穩穩地把輪胎抓牢。

曾經我習慣在深夜寫稿,常會失去時間意識工作到黎明,約莫第一班公車發車時,下樓走到不遠的巷口,排在那列上班族後面,假裝是來買早點的。提著熱呼呼的煎包返回住所,在漸亮的日光中吃著那袋宵夜。頂樓安置了觀看一座城市合宜的景框,天氣好的時節,我會站在陽台邊,聞著由社區公園飄上來的植物清香,感受萬物的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