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奇普的故事
他身材瘦高,長得白白淨淨,舉手投足卻有滑稽的喜感。在他叨叨絮絮的陳詞中,我辨識出一種魅力:你隱隱覺察這個人比其他同齡人都見識過更多。史奇普是從一所工專轉學過來讀哲學系的,大我兩屆,大概從我身上也辨識出一些特質 —— 我倆讀的科系都冷門到不行,而且都一心熱愛次文化。
您的數位閱讀序號權限期間為

他身材瘦高,長得白白淨淨,舉手投足卻有滑稽的喜感。在他叨叨絮絮的陳詞中,我辨識出一種魅力:你隱隱覺察這個人比其他同齡人都見識過更多。史奇普是從一所工專轉學過來讀哲學系的,大我兩屆,大概從我身上也辨識出一些特質 —— 我倆讀的科系都冷門到不行,而且都一心熱愛次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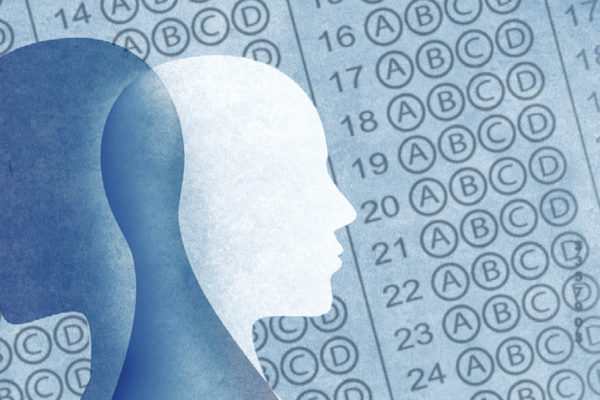
我是睡著了嗎?還是一直醒著?僵硬的身軀一點一滴沉入一座浮盪的水池,我的皮膚能清楚感受到卡其制服的觸感,右手握著原子筆(用我慣用的姿勢),在一間無窗的教室裡寫著鬆軟的考卷。寫下的字像湖心的漣漪在表面暈開,散成一團一團模糊的藍色,最後從書桌四邊掉了下去。我來回塗塗寫寫,考卷依舊一片空白,而且愈寫愈薄,愈塗愈濕……

三人小隊,移動起來應該比較迅捷,從「布新叉路口」往東行後,地勢漸漸變得破碎,在桃源營地每人多背了好幾公斤的水,重裝強渡連理山,那連理山啊!海拔 3,136 公尺,別被它浪漫的山名給騙了,巨石和樹根覆蓋著山體,路開得極陡,整座山的姿態極不歡迎訪客。登頂時我又氣又累,幾乎去了半條命。

他是樂團裡年紀最長的一員,已經 78 歲了,一頭白髮剪得整齊俐落,像手下的反拍節奏(backbeat)。有人說,他的鼓點是驅動滾石樂團向前的心跳,那浸泡著爵士底蘊的鼓點,而浪蕩不羈的吉他手基思‧理查茲(Keith Richards)是如此描述他和沃茨的關係:「音樂性上,沃茨像一張床,讓我可以躺在上面。」

而他等到的,只有咻咻的風聲和下一個日出。阿里、史諾里和莫爾當晚就被通報為失蹤人口,直到 2 月 18 日被官方正式宣告死亡,巴基斯坦政府每天都出動軍用直升機對 K2 山域進行大規模搜索。但直升機難越 7,000 公尺的高空,派人力救援只是徒增二次山難,眾人心知肚明,再強大的攀登者都無法在那樣的高度、那種氣候下熬過兩晚。

來聽講的有當時 K2 Project 的贊助者,隔著一面口罩,我約略能辨認出幾張臉孔。播放到一張我和攀登家阿果和元植在基地帳合影的照片時,我發現帶去遠征的那個紫色水壺,也被我帶來屏東。我把靠在電腦旁邊的水壺拿起來,向讀者說:「你們看!就是它,和我去過 K2 的山腳。」

他一手按壓離合器,一手猛催油門,右腳熟練地勾著打檔桿,與狹窄的山路周旋。車身右側不過一個輪徑寬,是又深又陡的丹大溪谷,如果一個打滑我就會抱著他一起落入萬丈深淵。但此刻我只能信任他的技術,相信他話語中沒有一絲要挖苦我的意圖。

這種「延後發生」,加深了意識裡的雙重現實感,如蘇珊‧桑塔格在〈愛滋病及其隱喻〉中所說:「有正在發生之物,亦有它所預示之物,即行將來臨然而尚未真實發生的不能真正控制的災難。這其實是兩種災難,其間存在空隙,想像力深陷空隙中,不能自拔。」

我一陣激動,叫出前天在嘉明湖畔拍的照片,湖心的範圍因乾旱縮小了。天使的淚珠——人們如此稱呼那座湛藍的高山湖泊,我記得自己切下草原,腳面踩著濕軟沙地的觸感,當時我在湖邊繞了一圈,心裡想的是,天使最近比較不傷悲。

作家,恐怕是最自戀的職業了,職業目標是讓自己的「分靈體」擺滿整座城市的書店,被放在醒目的位置,群書眾星拱月環繞著它。而一個好的位置(即作家在書店裡的地段),加上動人的書名、厲害的文案與漂亮的裝幀,或許就能吸引到讀者的目光,讓他低頭多看它一眼。

這球後來被譽為「世紀進球」(Goal of the Century),足球史上最邪惡與最美麗的入球,就誕生在同一場比賽,僅相隔 240 秒。馬拉度納成為歷史的載體,世界盃最後一個個人英雄,他憑一己之力替阿根廷奪下金盃,並以整屆賽事五進球、五助攻的驚人表現,獲頒最佳球員獎。

三十年後,另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我在國父紀念館的側門排著隊,準備入場參加第57屆金馬獎頒獎典禮。我把為了參加朋友婚禮買的黑西裝從衣櫃裡掏出來,打了個黑領帶,腳下是雙橘色的球鞋,這是我最接近「盛裝出席」的打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