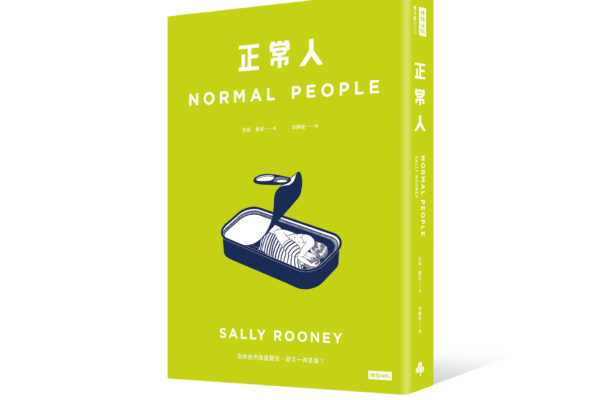更好的解答——詹姆士.霍根《星辰的繼承者》
各位若接觸過克拉克的作品(至少台灣曾出版過全套的《太空漫遊》和《拉瑪》系列,以及《童年末日》),就曉得這正是克拉克的特色:渺小人類在浩瀚的星際世界中面對更崇高、偉大的未知,並透過這種描寫帶來驚奇與震撼。1972年贏得雨果跟星雲獎的《拉瑪任務》(Rendezvous With Rama)描述一個無人、太空船般的圓柱體進入太陽系,人類試著探查當中的祕密,但就在依舊一頭霧水下,這神祕物體繞過太陽離開了、留下令人不安的暗示。NASA噴射推進實驗室工程師簡崔・李(Gentry Lee)寫了三本續集,把這系列變成以人物為中心的太空歌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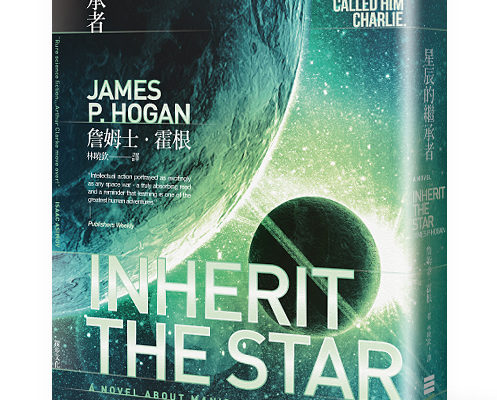
-1-600x4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