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足以成為普通的新奇」
就跟一句「非比尋常」便能把設計師快樂地捧上天,你也可以用「毫無特色」(加一點漠然的眼光)輕易激怒尤其年輕的設計師,甚至直接送他/她們下地獄。…… 設計的目標永遠是在「創造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在世上出現過的事物」。
您的數位閱讀序號權限期間為

就跟一句「非比尋常」便能把設計師快樂地捧上天,你也可以用「毫無特色」(加一點漠然的眼光)輕易激怒尤其年輕的設計師,甚至直接送他/她們下地獄。…… 設計的目標永遠是在「創造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在世上出現過的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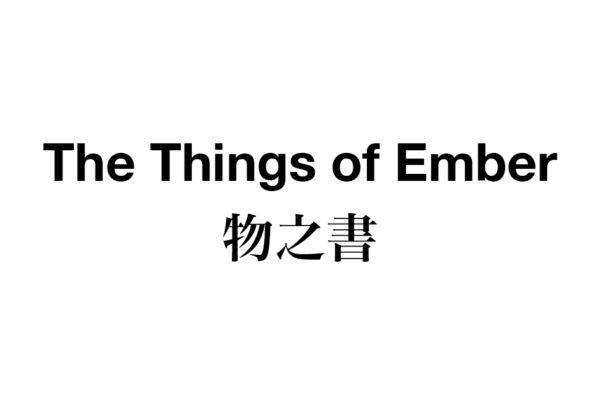
這些時候,我會感覺自己很無知。一種即使你到了五十歲,但之前藏那於腦中的前半閱歷,在比對新遇見的陌生情境時,其實永遠不夠調動,永遠在借著有偏差的記憶,試圖微調,但其實也不會有年輕時茫然無措,戲劇性的讓別人感到突兀或被冒犯的犯錯了。
我總在說:不,我不是那樣的。不,不是你們認為的那樣。

我總是習慣在醒來片刻就開始發呆。尤其愈來愈冷的季節,所謂異國情調不過是晨間的一縷冰冷空氣,從窗櫺縫隙悄悄鑽入面頰毛細孔。十八年了。如果從那刻以後的自己有了什麼新生意義,「新自己」如今也已成年。永遠記得當時的不安感,幾乎蓋過了興奮。這是我和「新自己」相遇的第一晚,與其說新奇陌生,不如說一切似曾相識 (déjà vu)。

於孔德過世的次年誕生、同樣是法國人的涂爾幹(Emile Durkheim,1858-1917)拯救了孔德的啟蒙視野,並繼承了實證科學的志向,在短短六年間奇蹟般靠著高超的創業手法與充滿想像的說服技巧接生了社會學。追根究柢,孔德雖然給社會學取了名字,但涂爾幹才真正靠「活用社會學」給了它能行住坐臥的肉身,百年後回頭想像他當年面對的時代思考慣性,仔細看他大膽細膩的創舉,仍舊只能自嘆弗如、讚歎不已。

「像水一樣吧,我的朋友」(Be water, my friend)李小龍多麽深不可測,無法擊倒。要以肉身優雅對抗體制化的規訓與懲戒、或者系統化的無聊生活,就必需練習面對生命時時刻刻不知如何是好的事實。而各種機遇都在訴說:你時時刻刻、自自由由可以準備重新開始。

理解涂爾幹的「迷亂」(Anomie)或韋伯苦惱許多人的「理性化弔詭」,這些恢宏深邃的「大哉問」也常被當成向他們學習的目標,但我不想要將心力放置於此——不是理當站在當代的時空座標,試著提出我們自己哪怕再小但真切的問題嗎?

或許人生真的不是由「得到什麼」所構成,相反的,是被「失去什麼」而牽引前進。從 20、30、來到 40 幾歲,每個階段我都曾被老天高高捧起後重重摔下。我遺失過許多比物品和金錢更令人慌亂失落的東西,像是對政治與社會的理想、對人的善意信任、對親密關係的認真承諾等等。而且,我不能只說自己被竊走了什麼,捫心自省,我也曾深深愧疚於自己帶走了別人的重要記憶。

我有位剛畢業的助理,生於 1994 年,曾是個足球迷。這得回溯到她唸高一、2010 年的世界盃。當時她迷上了西班牙的門將兼隊長卡西拉斯,這位傳奇人物不僅帶領西國奪冠,也是當屆金手套獎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