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冬季奧運會的主辦城市不再下雪
但是對冬季奧運會來說,這或許是個罕見的景象,因為溫室效應造成的氣候變遷影響,近幾年來冬奧主辦城市最大的煩惱反而是降雪太少。
您的數位閱讀序號權限期間為

像愛麗絲被白兔引導跳進了洞裡,某一天攝影師陳的發現他辦公室洗手間裡的窗口正對著柴灣消防局,提供了一個無所不知的視角,可以觀察到消防員在日常操場上的一舉一動:集會、清洗消防車、小學生參訪、排球比賽。樓層高度使得拍攝照片的距離拉長,將消防員壓縮成微型雕像,每日的紀錄讓圖像顯得抽象且重複,那個小小的窗戶打開了一段奇妙旅程的篇章。

制裁者是漫威世界裡最具爭議性的反英雄人物,他以暴制暴、除惡務盡。他背負全家滅門血仇,單挑大大小小的罪惡組織。沒有超能力,只有一身特戰技能。壞人懼怕他,但事實是連好人也不太喜歡他。

SHISHAMO毫無疑問是目前最具影響力的女子組合。這組平均年齡只有 22 歲的三人組合在日本年輕世代間擁有極高的人氣,甚至連主唱宮崎朝子的斜瀏海都成為高中女生的時尚象徵。來自日本川崎市的 SHISHAMO,到底有什麼樣的魅力呢?

阮越清的首部小說《同情者》獲得了包括2016年美國普立茲小說獎在內的各大獎項。無論讀者身處何方,這是一本能和任何遭遇分裂、衝突與偽善意識形態幻滅之所在呼應的小說。《同情者》談的不僅是越戰,更是一段普世的故事

在過去三年,美國奧委會做了許多改變,犯罪紀錄查核和防治虐待的教育訓練納入規定,今年3月更成立了「美國安全體育中心」(U.S. Center for SafeSport)專責處理性侵投訴,參議員也修法規定,任何疑似性侵投訴,就該即時通知當局,但那種為了勝利不惜一切的心態,或許需要更多時間才能夠扭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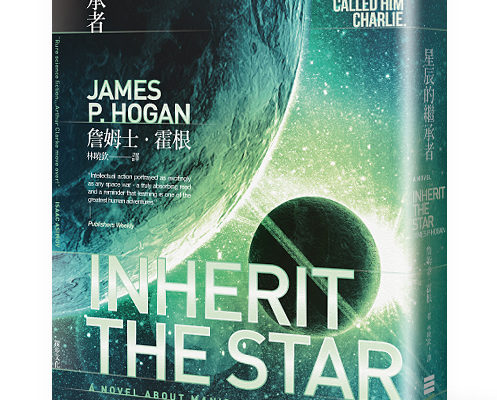
各位若接觸過克拉克的作品(至少台灣曾出版過全套的《太空漫遊》和《拉瑪》系列,以及《童年末日》),就曉得這正是克拉克的特色:渺小人類在浩瀚的星際世界中面對更崇高、偉大的未知,並透過這種描寫帶來驚奇與震撼。1972年贏得雨果跟星雲獎的《拉瑪任務》(Rendezvous With Rama)描述一個無人、太空船般的圓柱體進入太陽系,人類試著探查當中的祕密,但就在依舊一頭霧水下,這神祕物體繞過太陽離開了、留下令人不安的暗示。NASA噴射推進實驗室工程師簡崔・李(Gentry Lee)寫了三本續集,把這系列變成以人物為中心的太空歌劇。
-1-600x400.jpg)
楊凱麟的系譜之一是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其中楊凱麟在其名著《差異與重複》為我們畫下重點:真正的差異,不是跟「同」反義的「異」,而是將差異再度且一再一再「差異化」。換言之,所謂重複,不過是讓差異足以真正配得上差異之名的方法,所謂「差異的N次方」。是以,「虛構集」之名,與其說是致敬,毋寧說是種詛咒——如果我們認真看待波赫士,與認真看待「虛構」真正蘊含的威力的話。真正的作家不單是寫出被詛咒的作品之人(如波特萊爾、韓波、薩德、福婁拜、巴塔耶),他們更是對自己的作品以及自己下詛咒之人。一步即地獄,筆尖鑿開的現實,裂出的總是闢開腦門瞬間的眩暈光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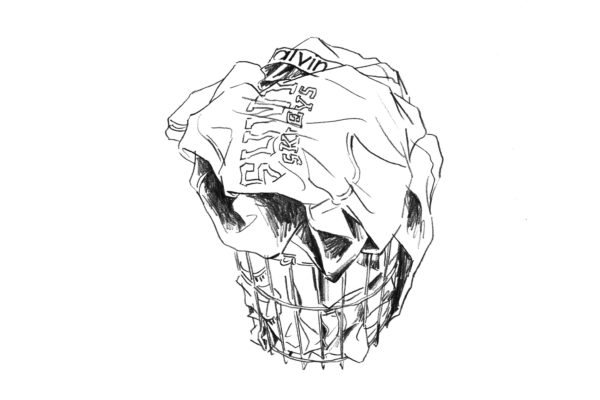
企圖捕捉生活瞬間,對手機隨身的人來說輕而易舉;我們總能快速製造許多「現場」也更加速地遺忘它。本期為《週刊編集》繪製封面的日本插畫家Norikazu Hatta,他的插畫作品是描繪攝影所沒有留下、日常生活片段間的縫隙。當那些時光的縫隙再次以筆畫呈現時,會令人恍然大悟,自己曾擁有過那些微小卻重要的事情

知道 TAI 身體劇場的編舞家瓦旦・督喜(Watan Tusi)想以「酒」為創作主題,是一年多前的事。當時我想當然耳地認為,瓦旦必然處理原住民飲酒文化如何被曲解,而看似「酗酒」的形象又是怎麼被社會結構擠壓塑成的。但這當然又是我的一廂情願。在這個議題充斥、抗爭不斷的年代,沒人規定藝術家得像社會學家那樣用創作剖析社會,但這似乎是種政治正確不過的選擇,只是同時,藝術家也會面臨「與其在劇場談議題,為何不上街頭參與運動」的質疑。在公理與正義之間,在運動與美學之間,藝術家彷彿也遭遇夾縫兩難的存在問題。

劇場表演課入門,第一件事就是玩遊戲,透過各種活動開發潛能,包括身體反應、協調、接收、傳達及聲音運用等。這個階段,許多人總在第一時間感到抗拒,畢竟遊戲需要的能力,「出戲」後看起來往往一無是處。舉例而言,有個遊戲讓眾人圍成一圈,讓中間的「鬼」隨機指定圓上的人模仿一種動物,並要在鬼快速數十前完成;動物共有三款,每款由三人組成,也就是說,當中間的人被指定時,左右兩人也須即刻反應,數十後仍未完整反應者即判失敗,由他接替當鬼。這叫做「動物園」。類似遊戲在劇場練習比比皆是,但我們為什麼做?

舞台上斜斜的灰色表面,躺著裸體的人。好似沙灘日光浴。突然,太空人出現在遠方,原本令人聯想到沙灘的灰色舞台,驀地成為陌生星球,劇場靜的出奇,只剩太空人濁重呼吸聲,太空人把星球表面開了個洞,石頭漂浮出來,太空人拉出一個裸體人。藍色多瑙河的音樂響起,令人想起科幻片經典《2001:太空漫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