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土
實景幻覺相雜,我躺在薄簾相隔的臥鋪裡,回想離岸 20 分鐘內所見,身體卻還像在甲板觀夜,遊蕩支撐與順從之間。閉上眼睛,精神強收在體內後,船體抬升、落下又抬升的波動更加明顯。為什麼浪是「掀」起的?場景本沒有一絲風波,是因為離開陸地,平滑的日常感覺才一層一層被揭開。
您的數位閱讀序號權限期間為
實景幻覺相雜,我躺在薄簾相隔的臥鋪裡,回想離岸 20 分鐘內所見,身體卻還像在甲板觀夜,遊蕩支撐與順從之間。閉上眼睛,精神強收在體內後,船體抬升、落下又抬升的波動更加明顯。為什麼浪是「掀」起的?場景本沒有一絲風波,是因為離開陸地,平滑的日常感覺才一層一層被揭開。

哼歌是日常必要情趣,從捷運站走回家,或騎腳踏車去還書,總有幾首常哼的歌。哼是一張薄紙上的鉛線。自己不知情,旁人不明白,模糊但自由的聲音,在口罩裡逗留。我與Saki吃飯採買的時候,也常在路上自動哼起歌。只是許多時候我會像冷靜的自販機,落出完整一首兒歌:一隻蛤蟆一張嘴,兩隻眼睛四條腿。乒乒乓乓跳下水呀,蛤蟆不吃水,太平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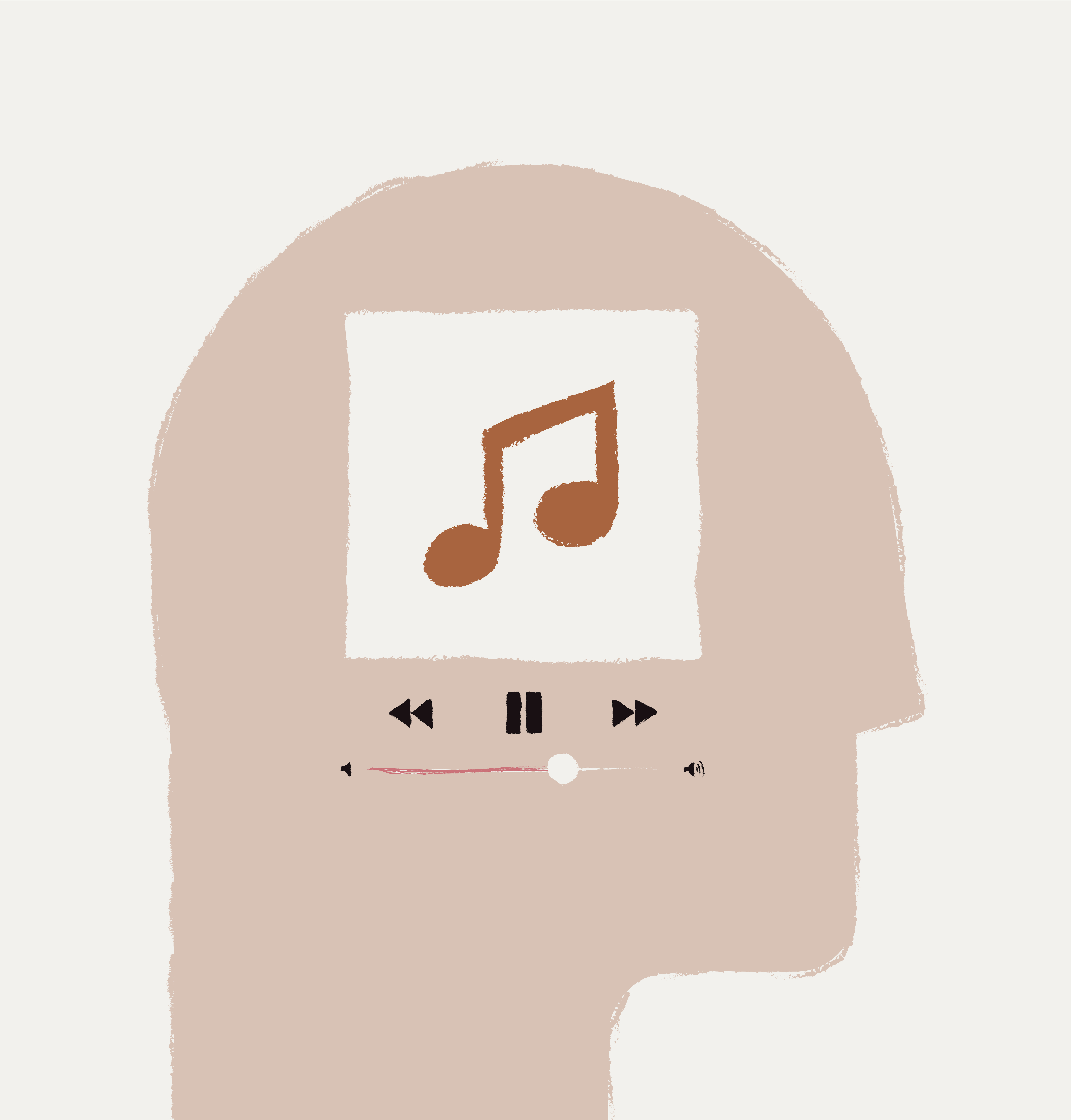
聲音有它的指紋,聽歌識別軟體仰賴其運行。記憶的指紋識別什麼?那台掌上的磁帶隨身聽,不只播音,也能錄音。紅點●跟著▶一同按下,我書房內的聲音指紋被那小黑盒含起來:少年正在唱鄧麗君/王菲的〈雪中蓮〉。他試著擴張口腔,讓「飄」這個字拉長,移動位置,像電扇擺頭②的微風,散布到空間裡。中等尺寸的雨珠打在頂樓鐵皮,一連串失蹤的形聲字。蓮花開在雪中間。多少的希望,多少的心////。哥哥吃飯了。他的音響止於此。

小學三年級那一年,綜藝節目裡千葉美加初登場。從日本來台發展的她,出道曲〈青春起飛〉裡有兩句中英混合的歌詞:「It’s so easy, easy to be happy. 這世界,任你去陶醉,去流淚!」看完張菲與費玉清主持的《龍兄虎弟》,美加熱情的歌聲留在我的小身體盤旋。字面看來很傳奇,其實只是耳朵蟲在我身上初次發威,粉筆沙沙滑動的小春天裡,我是一條陶醉而惱人的蟲。

無情人留給台北了,歌詞的小結論是:「愛本來是孤兒」。但你想的不是對愛絕望,人生無侶。你想要讓一顆字也是一顆孤兒。我。心。車。水。它們素顏,自我壓縮,分別選擇一首歌來引用,抽成真空包。先前你讀過一篇論文,寫到港歌,時代,戀愛與城鄉移動之間的因果。

收看《浴火鳳凰》的那個暑假,我也開始學著唱歌。在新竹姑姑家過暑假,姑姑一家午後慵懶地在臥室小寐,我卻想暗暗找個地方伸展自己的聲音。門口落地窗垂著厚重的提花窗簾,硬紗質地的直立百葉。我用兩層簾子滾裹自己,試圖形成緊實的隔音。窗簾細小的連珠繩交纏,商量著,我放膽地使用假音歌唱。像一尾雨前的水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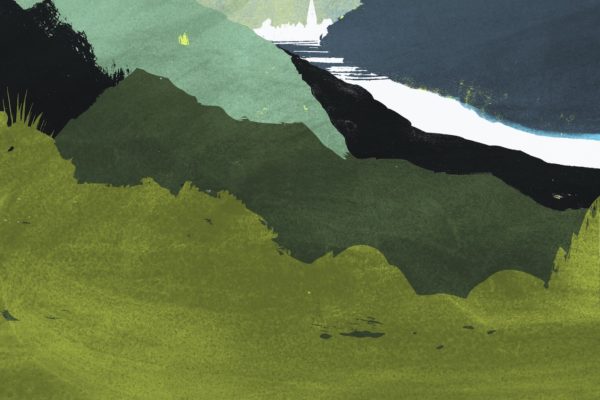
濕地是 Kanaluvang。kana 是那個,luvang 是洞穴。「我認得 luvang 耶,在關於『山川地理』的詞彙包裡有學到。」但姑姑說,這個洞穴,並不是山洞,而是地上凹凹凸凸的坑洞——我想像濕地的小車路與小車路之間,牛與鷺活動的場合,草木遮蔽下還有另一種地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