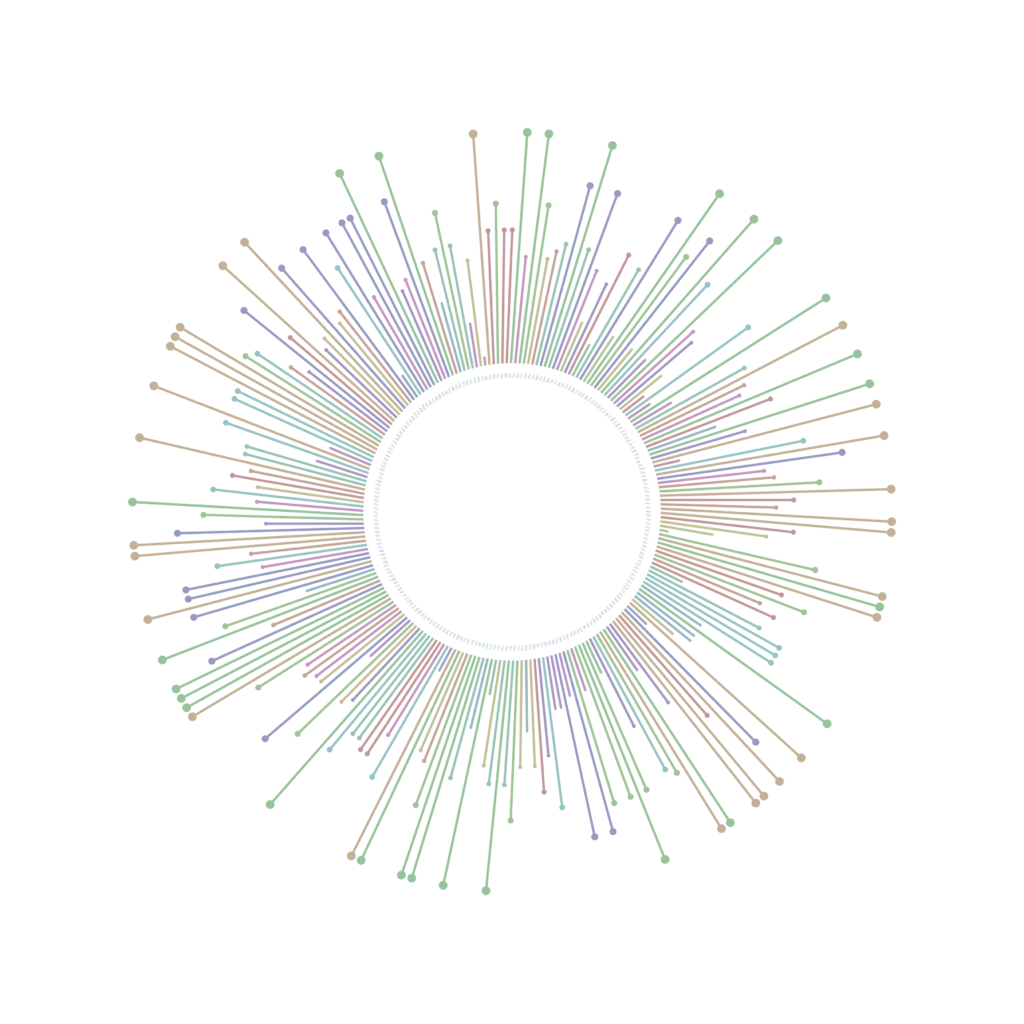藝術家吳梓寧最近於台北當代藝術館沈柏丞策劃的「蓋婭:基因、演算、智能設計與自動機_幻我;它境」展覽中,展出《捕蠅草人改造計畫 01》(以下簡稱《捕蠅草》)這件錄像裝置作品。藝術家除了以動畫的方式將女性外陰圖像合成在捕蠅草不斷開闔的葉片上,希望架橋消化器官與生殖器官的功能之外,還期待透過植物與人類器官層次上生成甚至共用的可能性,突破單純只是語言隱喻層次上的限制。就此而言,藝術家研究了捕蠅草消化相關基因與人類基因中性功能相關部分,發現人類的精胺酸酶有著與捕蠅草消化液類似的蛋白質晶體結構,所以在展場中展示這兩個部分的基因圖示,希望顯示原本語言隱喻上的想像,在後維納斯的生物科技時代,具有基因層次上的物質性基礎。

性、慾望、身體
在《捕蠅草》展間牆上引述了達爾文描述捕蠅草的話:「這植物,俗稱『維納斯的捕蠅陷阱』,它快速且有力的運動,是這世上最美好的事物之一。」對藝術家來說,她希望透過《捕蠅草》這件作品,提出一種「後維納斯身體」的概念,這個身體可以設置陷阱來獵捕慾望。或者更清楚地說,「捕蠅草人」這種後維納斯身體的設想,是一種慾望獵捕的機器。如果是這樣,維納斯式的身體到底具有什麼特質?捕獲慾望又是什麼意思?為什麼藝術家會構思能夠捕獲慾望的機器呢?
或許維納斯這個女性神祇的形象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發。維納斯不只是一個現代意義下的「女性」,還擁有前現代意義下的「神祇」特質。換句話說,維納斯具有女性與神性的雙重性,我們無法單純以「現代意義下的女性」來理解維納斯的行為。雖然在前述達爾文的話裡,維納斯並不是放在「現代女性」的意義下來使用的,但是當吳梓寧將性、慾望與身體放在同一個議題平面上,並將維納斯/後維納斯當成是歷史分期的方式,維納斯與身體的關係就成了《捕蠅草》這件作品的重點。從這個角度來看,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對於性、慾望與身體的思考,為我們指出理解《捕蠅草》的方向。
對布希亞來說,只有到了「現代」這個時期,女性才以對立於男性的方式成為一個獨特的、結構化的位置,而每個被認定為「(現代-)女性」的「個體」,都基於這個結構的組織方式,將性別的區分(男性/女性)當成「首要的區分」來組織對人的認識。在這個區分中,「男性」界定了這組區分的內涵,所有不被認定為男性的特質,都被認定是女性的;或者更清楚地說,女性不過是「非男性」而已。但是從「非男性」到「成為女性」的過程中,也就是從「關係中的客體」到「自我認知為主體」的過程中,由於現代時期提升了性與慾望兩者在首要區分下的重要性,所以現代女性被指認為「擁有性的祕密與源源不絕慾望」的個體,占據了性別這組區分的真理(truth)。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正是因此把女性標誌為「被指定的」(assigned)與「被壓抑的」。布希亞認為佛洛伊德的做法,是以解剖學式的思維,在「性」這種功能性的關照下,以性器官的差異來區分性別,所以我們會在佛洛伊德的理論中,讀到性與慾望在親密關係中的決定性影響。
相對於佛洛伊德這種解剖學式的女性理論,布希亞認為,不管是現代之前或後於現代的女性,都並非以「性別」對立於男性。「女性」因而不必然是本質性的、性與性別意義下的、對立於男性的另一個性別。維納斯雙重性裡的神性,恰恰是解剖學觀點下,所認為現代時期的女性不具有的特質。以布希亞的話來說,這是一種由「陰性氣質」(femininity)所展現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恰是因為這樣的不確定性,在親密關係中,可能誘發許多相異的人際關係模式。尼可拉斯.魯曼(Niklas Luhmann)曾經在這樣的基礎上,指出在西歐從前現代時期往現代時期過渡的時候,親密關係與性這兩者非單線的進程。在這些嘗試發展不同親密關係模式的演化中,我們可以辨識出慈悲的愛情(amor benevolentiae)、肉慾的愛情(amor concupiscentiae)、浪漫的愛情……等等這些曾存在於歷史上的不同類型,並且最終在現代早期收束到炙烈的愛情(amour passion)這種關係,並用「激情」(passion)這種語意來對抗家庭與社會控制親密關係(也就是「婚姻」)的企圖。
現代之後的「女性」與後維納斯的身體
不過,誠如魯曼提醒我們的,當前的我們所面對到的社會情境,已全然不同於現代早期。當時(特別是在浪漫主義時期)所在意的是將「個別個體的自我」理解為「超驗的自我」,也就是作為不被它者或系統所束縛的自我,因而在親密關係上,我們尋求不同於婚姻關係的愛情關係,作為這種超驗自我的行動領域。但在當前的時代,我們在意的是「我的自我」,在愛情之中,這樣的「我」是作為自身愛情的根源而行動。就此而言,「我」必須是「我自己的愛情行動」的理據。恰恰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女性不再只是性別意義下的女性;不再只是「被主體化之客體」的被動女性;當然也不是複製陽具霸權的女性,這種陽具化的女性只不過倒轉了「男性/女性」的區分,卻沒有離開性功能支配與壓抑的統治邏輯。相對於前兩種仍然停留在「男性/女性」區分之中的女性,當前這個時代的女性,並無法涵蓋於「男性/女性」這組性別意義的任何位置,或者也可以說,是這組區分之外的黑洞。
只有在性別意義下的「男性/女性」區分不再有效的時候,作為女性性徵的外陰,才能夠脫離「器官」原本功能性/性功能的束縛,與捕蠅草開闔的葉子(葉子並不是性器官)重新組裝,形成新的器官。《捕蠅草》中構想的新器官,並不是長在人身上,而是長在植物身上。「性化」與「性別化」已然跨越物種,蔓延到被認為是最被動的植物身上,再也沒有生物的身體不具有性化與性別化的特質。不過,恰恰是全面的性化與性別化,才導致了這種「後維納斯身體」的誕生。後維納斯身體並不是現代時期解剖學式的身體,而是現代之後基因科技所創造的身體。在世界已然全面系統化與功能化的現在,吳梓寧所創造的、擁有後維納斯身體的生命,企圖重新獵捕這些在現代時期才固定下來的二元對立,為我們進入下一個社會預先做好準備。而《捕蠅草》中這個同時擁有捕食與性功能的器官能夠捕獲的,是布希亞所謂的「全神貫注於享受需求的慾望」(desire, all of which is channelled into the demand for enjoyment),也是現代時期這組「男性/女性」性別意義的區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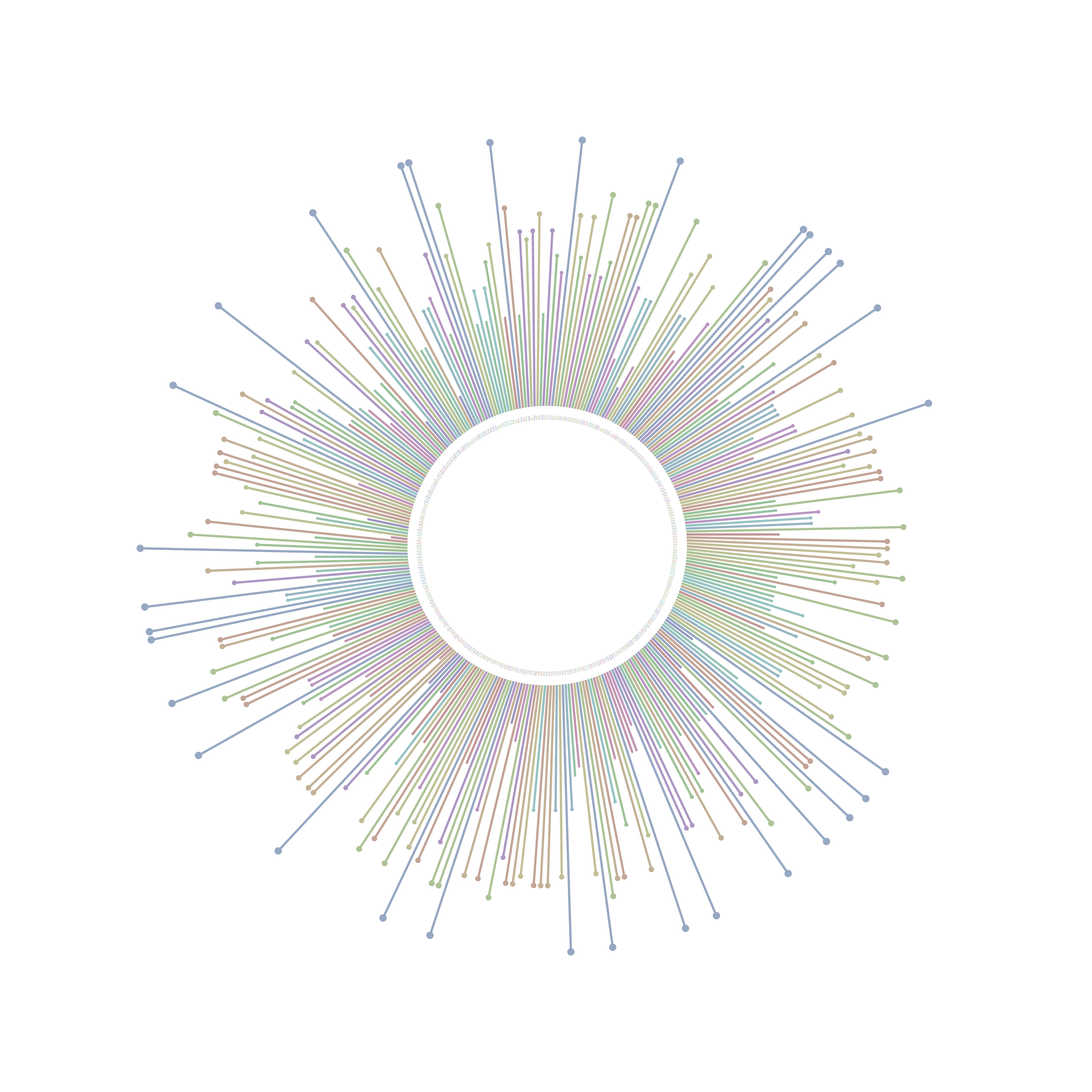
不同於 2018 年的展出版本,吳梓寧延伸創作《5A24》與《1PQ3》二件新作,透過基因密碼子的20個蛋白質代碼,將同樣出現在 CGI 模擬影片中的「捕蠅草消化液」與「人類精氨酸酶」的氨基酸序列進行程式演算的視覺化。(吳梓寧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