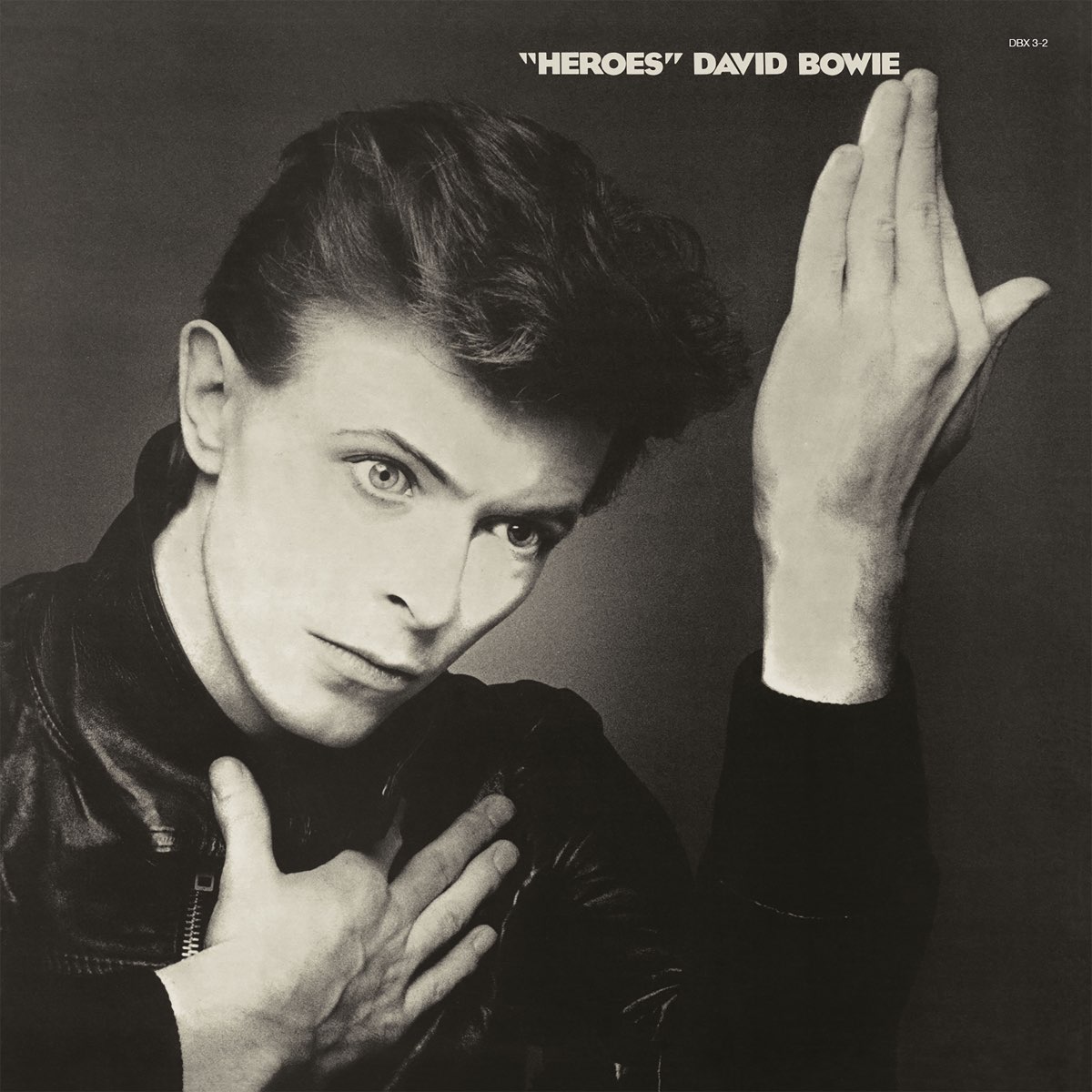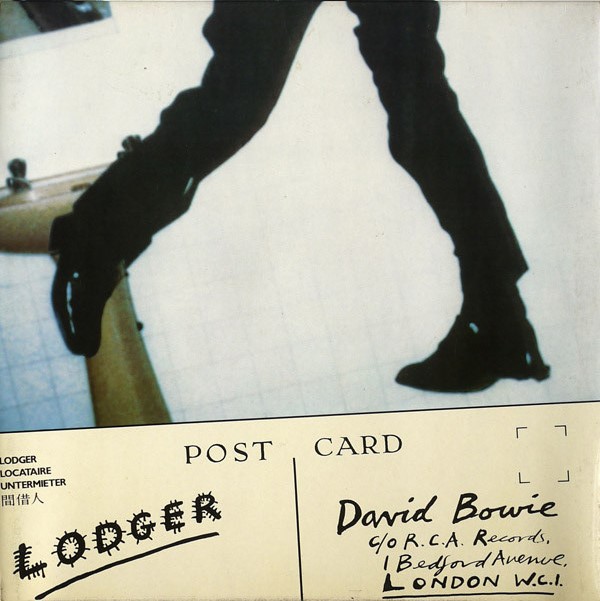我在情感和社交方面嚴重衰退,認為自己極有可能成為搖滾樂下的犧牲品之一。我很確信,如果不做出改變,就絕對沒有辦法在七〇年代中倖存,同時我也非常幸運,能夠得知內心深處的某個地方正在凋零,我必須做出更加劇烈的事情來使自己擺脫這種狀態。
——大衛・鮑伊,1996
遠離美國
為了尋覓創作靈感,鮑伊在1974年前往美國,並形容自己是一隻誤闖進牛奶盒的蒼蠅,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盡可能地汲取周遭的文化。隔年發行的《Young Americans》成功將費城靈魂樂和放克節奏納入囊中,甚至成為首位在黑人電視節目《Soul Train》登台的白人歌手。然而,如同當時音樂圈的多數人,鮑伊也難逃毒癮摧殘,在1976年錄製《Station To Station》時身心狀態每況愈下,同時與安琪(Angie Barnett)的婚姻也亮起紅燈,這張專輯因此被視為他所發出的求救訊號。精疲力竭之際,他決定前往當時實驗性音樂盛行的歐洲,譜下影響後世無數音樂風格的 「柏林三部曲」。
《Low》作為三部曲的開端,是鮑伊極力想逃離美國的象徵,是精神問題和毒癮的倒映,他呆坐在潛意識的房間內等待靈光一閃,無話可說、無事可做,即使自閉憂鬱,卻難掩對新生活的一絲期待,整張專輯因此染上了一層濃厚的疏離色彩和強大張力。
進駐城堡
1976年5月,鮑伊接連於溫布利舉行了幾場演唱會,並在後台與布萊恩.伊諾(Brian Eno)見面,後者同樣在搖滾樂和音樂製作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兩人相談甚歡,發現彼此皆著迷於當時德國的實驗音樂場景和泡菜搖滾(Krautrock)。隨後伊諾前往鮑伊在瑞士的住所,共同策劃下一張專輯的內容,並預訂了法國埃魯維爾城堡(Château d’Hérouville)錄音室作為主要錄製地點,此外也聯繫了長期合作的好友兼製作人托尼.維斯康蒂(Tony Visconti)前來參與,正式建立起新專輯的核心金三角。
9月,鮑伊帶著參考資料走進錄音室,包括先前為主演電影《The Man Fell To Earth》 錄製的電影配樂、協助製作伊基.帕普(Iggy Pop)專輯的剩餘素材以及在瑞士住家寫下的草稿,這些材料非常零碎,因此大部分時間將會花費在創作上。正式開工後,樂手們被要求圍繞著和弦指令開始即興發揮,並不斷嘗試各式風格,當伴奏完成時會進一步經過電子化的處理,因此《Low》幾乎捨棄了所有的自然原聲。
維斯康蒂使用了各種效果器、過濾器以及錄音室技巧,專輯中帶有未來感的塑膠鼓擊音色便是出自他手;再來一個重點便是伊諾的 EMS Synthi AKS,不同於新時代的合成器,EMS 本身並沒有配置琴鍵,只有各種球柄搖桿,還有一塊布滿按鈕的控制台,將各種參數相互連結起來,搭配搖桿便可以製造出許多扭曲的聲音。伊諾還為專輯製作過程帶來迂迴策略(Oblique Strategies),這是伊諾與藝術家彼得.施密特(Peter Schmidt)共同為藝術工作者開發的一套卡牌,當遇上瓶頸時,上面會有各種指示,來幫助創作者跳脫停滯的思考迴圈。
錄音的最後階段,鮑伊會站在麥克風前做測試,在各種不同的情緒層面上嘗試不同的發聲,以找到最適合該歌曲的風格,而一旦找到了答案,便能確保每一塊拼圖都落在正確位置:器樂將變得立體,歌詞也能如百花綻放,展現各自的美妙姿態。
起初鮑伊和伊諾打算將專輯命名為《New Music: Night and Day》,來表達 A 面與 B 面的對立之意,即一面是節奏和合成器導向的流行歌曲,另一面卻是靜謐的環境音樂。《Low》中的每首歌曲皆帶有難以捉摸的特性,時常在聆聽者才剛進入狀況時,歌曲便突然淡出結束,像是三分鐘熱度過了,覺得一切索然無味、便果斷轉向別的目標;這張作品也不像一般專輯有一個緊扣的主題曲風,每首歌都個別獨立且支離破碎,與上一張專輯《Station To Station》的強烈黏著感相反,可看出《Low》是反映鮑伊當時身心狀態的一面明鏡,象徵一個孤獨和退縮的冷漠世界,思維的碎片隨風擺盪,語言和情感極度壓抑。像在〈Breaking Glass〉中,鮑伊拋棄先前擅長的敘事,重現垮掉派作家威廉.布洛斯(William S. Burroughs)的剪貼風格,將散落的歌詞重新拼湊成極簡的隱晦字句;器樂演奏上也是如同多道平行線,彼此拒絕握手言和,這樣的分裂完美彰顯鮑伊自身精神狀態的不穩定。
前進柏林
到了9月底,由於錄音室的服務糟糕,加上鮑伊和一些樂手宣稱城堡鬧鬼,於是團隊決定啟程前往柏林圍牆旁的漢莎錄音室(Hansa Studios)。在這個經歷戰敗重創,導致文化、藝術、人民被分割的城市裡,鮑伊將當地藝術組織「橋社」(Die Brücke)的表現主義應用在音樂上,這種畫派有其作畫哲學,拒絕客觀描繪風景,選擇直接將內在情緒反照在畫布上,除了影響 B 面冷色調的環境音樂風格,更促使鮑伊譜寫出專輯中唯一全程在柏林完成的歌曲〈Weeping Wall〉來描繪人民與圍牆之間的苦難。而後,鮑伊更在這個「世界海洛因之都」成功戒除毒癮,停留了將近兩年。
《Low》象徵著鮑伊正式踏上美學重塑的道路,將過往的舞台人設全數捨棄,如同新生兒誕生於荒原,試圖接觸陌生環境中的人事物,手邊沒有任何地圖導覽可循,只能憑著本能摸索和學習;那是一個文字和語言尚未系統化的未知世界,是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重疊交集,既是前進,也是後退,是一切矛盾的集合體。這讓《Low》沒有沾染上時代的氣味,至今聽來仍無以名狀,而在這趟尋求自由和救贖的旅程中,鮑伊將再次獲得取之不竭的靈感,將自己推上生涯的又一顛峰。
.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