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確幸
The Things of Emb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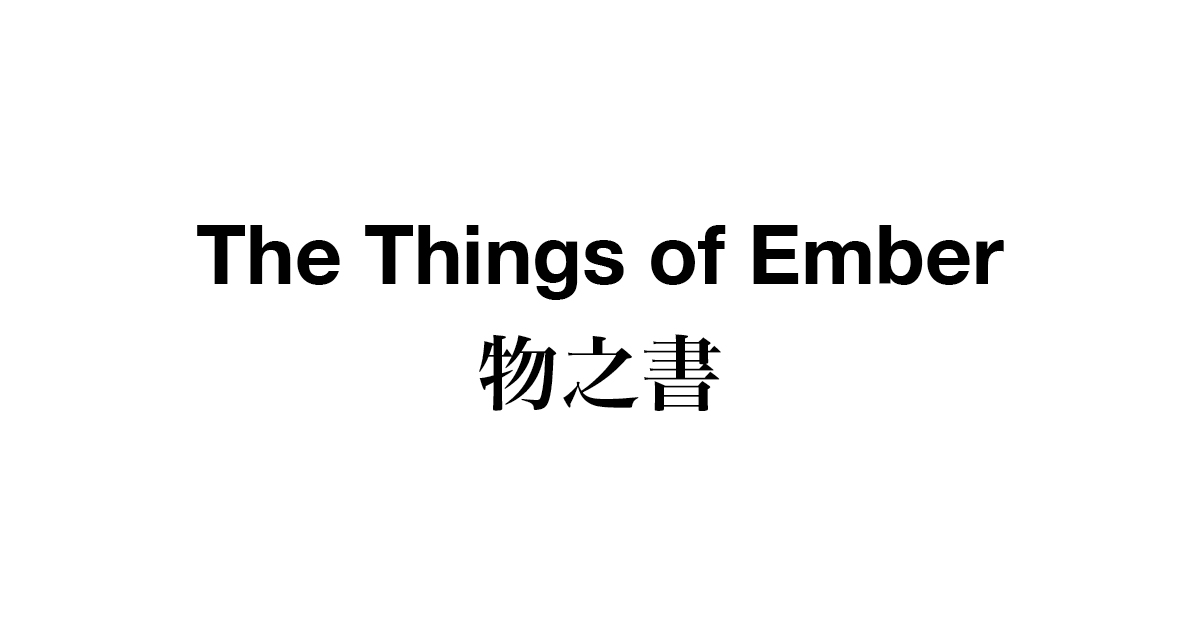
落花積地寸餘,游人少,翻以為快。忽騎者白紈而過,光晃衣,鮮麗倍常,諸友白其內者皆去表。少倦,臥地上飲,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為樂。偶艇子出花間,呼之,乃寺僧載茶來者。各啜一杯,蕩舟浩歌而返。
我們不會說袁宏道這是小確幸;一如我們不會說「飛羽流觴」是小確幸;說阮籍、稽康這些哥兒們是小確幸;宋人用鹧鴣斑窯變黑釉碗鬥茶是小確幸;或說周作人是小確幸。但我們會說在台北青田街綠光盈滿的巷弄咖啡屋,喝一杯奶油押花了一朵銀杏葉的熱拿鐵是小確幸,或兩個女孩兒租間店面賣花,這是小確幸?為啥?老實說,以我這樣年紀的大叔來說特別怕和「小確幸」沾上邊。
雖然確實我長期的上工地點,都是在那窗玻璃倒映小巷爬牆紫藤和魚鱗黑瓦老屋,會有鄰桌美少女,美麗店貓,木材和形狀都美得像女人窄肩流墜的小桌椅,那空氣中充滿烘焙咖啡豆的焦香味。我可是覺得我每天拿筆在影印紙上,無中生有的寫出字來,那幾乎是可以聽見兵馬轟隆轟隆、甲冑鞍蹄衝奔的聲響,或工廠裡機器旋轉、切割、擠碎的冰冷金屬聲,它是充滿暴力與瘋狂,高強度衝撞的活兒。但確實常常坐在那兒,偶從書頁抬起頭來。
你感覺時光暫停,身邊各桌的人影突然像被抽去纖維質,湯裡暈糊金光的南瓜塊。你也會想:他媽的,來日大難唇乾舌燥,將來一定會某個逃難貧困時候,無比懷念哀感的就是現在此刻眼前這一切吧。你會說這是「小確幸」,因為它確實和整個大的話語脈絡切斷了。那個網路纏繞的政治、社會、權力關係、階級資本,它也跟那卡夫卡〈城堡〉式的永遠和它打交道也只是迷宮打轉的,各種,你身陷其中層層縛綁的學校、醫院、法院、交通裁決所,甚至,那些每天發生的社會兇殺案強姦案政客帶女助理開房間餿水油被爆,所有這些唧唧歪歪煩人的事都切斷纜繩、蛛網、網絡 ADSL 線,你變成漂浮在外太空的小小宇航艙,甚至你和袁宏道、阮籍、稽康那些人不同,你連一個敘事的或抒情的自我戲劇化大傳統都切斷了。
他們做那樣的事,後頭有一個沉鬱苦悶遠遠超過個人身體、心靈的時代的粗暴「時代的輾碎機」,一整個朝廷階級品秩、鳳鳥,或走獸刺繡官服挨擠列隊,像 DNA 鍊一個嵌銜一個,沒有一個腦袋可以脫離這龐大老鐘的運轉機械,只有那幾個牛逼傢伙,脫隊向後轉,那個反轉 「佯瘋」後面根本是一根汽車傳動軸那麼粗的傢伙,捅進帝國空洞、異化、將個體成為小小傀偶,那麼大的擰勁,那個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的形上演出成本何其大?
你坐在咖啡屋喝杯咖啡,誰理你,你只是跟千千萬萬個喝咖啡的人一樣。我的老師紀蔚然先生日前恰在一文章提到「小確幸」:「如果『小確幸』代表對『幸福』不貪心、掌握可觸知事物、保住目前所有,那麼『小確幸』的意義就是接受現狀。現狀好時沒問題,現狀愈來愈差怎麼辦?雖然世事瞬息萬變,雖然有很多看不到的人正在受苦,有很多聽不見的人正在哀號,『小確幸』卻教我們不要管太多、不用想太遠,要聚焦於自我和當下,因為現在可是自身難保的危險年代啊。有些人確實自身難保,有的甚至三餐不保,但行有餘力者仍屬社會多數,可一旦這些多數,包括一般人、官員、候選人、媒體、網路社群、廣告、作家,不時將『小確幸』掛在嘴上,那些不公不義的事只怕會變本加厲,而且總有一天會輪到你我。」這讓我猶豫躊躇起來,確實我可能在寫這篇文字之前,對「小確幸」這個詞是模糊,如公路電影車窗外閃瞬而過的「時代的碎修辭」。
也就是它不是「我的時代」的感性發明,但又在我正進入未來的流動風景,像電塔、高速公路遮蔽天空的水泥長龍,也許坐在牛車上講手機的老頭,或巨大看板的銀行廣告。它已改變了我對「田野」的地景構圖。我想像我那個年代對現代文明之疲憊、厭惡時將自己投擲到那「流浪者之歌」的空景展開,才發覺其實這個流浪之途已被⋯⋯像公廁, 那麼多人來排泄過他們「對現代文明之疲憊、厭惡」。
它回不去的已被敘事框鎖成「人在冏途」。
電影、爛電影、臉書,或微博微信無數轉貼的異國美景,像宇宙星塵數量那麼大的,吉光片羽的陌生人的怨念,委屈、一瞬之嘆、愛的告白、炫耀的定格、我肏你,或陰暗猥瑣的孓孑形態。
想旅行的夢,小孩小狗的「愛的此在之証據」,何其小,對你個人而言,那麼巨大的「事件的360度環場」光陰充滿觸鬚全打開的時刻,當你要按下手指送出到那無垠海洋無數菌藻,瞬生瞬死交換著它們短短的基因段記憶體裡頭,你便知道這個傳輸檔,渺小到存在了等於泡沫破滅那一瞬:「念天地之悠悠」的億兆倍的「獨愴然而揮發」。
10的N次方的卡夫卡城堡,鑲嵌更繁複錯綜的資本主義蜂巢蟻窩,更不可能撼動的強權秩序,滲透到更微血管細微神經末梢個人隱私。潛意識的美感、快樂、夢、正義的集體化,鋪天蓋地,無「個人」完整裡外可以爬梳比對記憶 「此刻的我是一個完全自由或意義完足的存在」。
那時「小確幸」的「小」相對那個無邊際無個體,「確」相對那個可能所有意義、感性、詞語、影像都有偽造汙染之嫌疑。那時的「幸」兀立在那個大峽谷前的「我」洶湧召喚的,或是這樣全景幻燈,無遠弗屆,既宇宙爆脹同時又濃縮隱喻所有人痛苦哀愁哭泣耳語之噩夢。那個「再不可能真正爽颯、快樂、兩眼澄澈」的不幸現代人。自我幾乎一意識到「啊!這個是現在的獨一無二的我」,便瞬間崩散化為煙塵。
美感、美學的建構也如同集體農場飼養槽整桶整桶傾倒進去的化工配方。這麼想「小確幸」這個意念最初被發明出來,其實或近似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裡的薩賓娜,在那全國鋪天蓋地喇叭播放革命進行曲的遊行隊伍脫離,鑽進小巷,信步走到一墓園,一群老人,對著那死者唱著優美古典的哀歌。那是一種「連禱」的吟唱形式,彷彿死者不忍離世,一再回頭留連,而老人們也用那一陣一陣的疊唱,和他送別,既纏綿又節制。昆德拉說:薩賓娜在這一刻感受到美,因為它和整個群體那種強制而平庸的美感孤立且疏離。如果那年代有「小確幸」這個詞,且並不如後來一被孵育出來的「個人的剎那時光」便被商業傳媒如補撈螢光烏賊的巨網,撈進那集體複製的加工艙,那最初時刻的一聲嘆息的那麼小、那麼珍惜的(就像白流蘇在整座城陷落的故事結尾,踢進床底的蚊香盤吧?)個人屬於自己的什麼,它未必是和時代的、眾人的苦難無感脫離,它反而確定這整個龐大機器不能整個收編進冷酷死灰的,輕盈飛起的一個反手的姿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