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 年 8 月 15 日開始,原訂三天(最後變成四天)的胡士托音樂節(Woodstock)是爾後許多大型音樂節的原型。音樂人暨專欄作家鮑布・史丹利(Bob Stanley)聆聽新發行的胡士托音樂節實況紀念專輯,重新梳理那「和平與音樂的三日盛會」背後的真實聲音

幾週前,我的 Twitter 頁面上充斥著懷念 1985 年「拯救生命演唱會」(Live Aid)的動態。如今,這場演唱會被視為音樂很糟的白人救世主音樂會,但還是很多人想念史班杜芭蕾(Spandau Ballet)主唱東尼・海德里(Tony Hadley)的皮風衣,以及皇后合唱團「沒有時間給輸家」(No time for losers)的驚人哲學。我活過那個年代,我記得一群怯懦、年華老去的搖滾巨星是如何費盡全力拯救自己的事業。好啦,我那年 21 歲,超憤世嫉俗,但我確實在那個當下,在電視上看著一切展開。我瞭解「拯救生命」。
胡士托音樂節於 8 月中剛滿五十周年,是「拯救生命」和其他大型音樂節的原型。它的文化重量於過去幾十年來載浮載沉,全看你跟誰談論這件事——要嘛它是 1960 年代反主流文化的高峰,要嘛它是一場被雨打溼的夢。胡士托那年我只有 4 歲。1970 年代時,胡士托原聲帶唱片會在朋友家裡出現,電影每年都在電視上播出,我的世代認為自己瞭解胡士托音樂節,卻未曾親臨現場。但電影是不完整而失序的,部分情節跟《波希米亞狂想曲》一樣全是虛構的。
1969 年 8 月 15 日,星期五
胡士托音樂節五十周年紀念專輯甫於 8 月發行,一共 38 片 CD,幾乎可說是完整重現當年實況。因為其他表演者當時幾乎都困在車陣中,為胡士托開場的民俗藍調歌手瑞奇・海文斯(Richie Havens),便曾宣稱自己「表演了將近三小時⋯⋯我唱了所有我知道的歌!」現在我們知道,他只唱了 45 分鐘。這是一部聲音實況紀錄,連舞台上的公共廣播都錄進去了:「艾力克・克林伯格請打電話回家⋯⋯丹尼斯・戴奇請打給你的妻子⋯⋯來自波基普西的凱倫,請帶血壓藥到攤商處與哈洛德會合⋯⋯」我連續三天一口氣聽完了 38 片 CD。

「各位女士與先生,全世界最美麗的男子之一。」這是主持人對海文斯的介紹。「妙妙妙,你們好嗎?你們聽得見嗎?妙、妙極了。看到這麼多人聚集在一起感覺真好,對吧?妙極了。」所以,也許胡士托沒有披頭四(或住得很近的巴布・狄倫),卻有海文斯唱著〈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彷彿這首歌是在一個破小屋裡寫出來的。他接著唱了堪稱完美的〈Freedom〉作為安可曲,後來在電影裡成為高潮片段之一,歌曲中片段式的吉他與康加鼓聲是九〇年代末期節奏藍調的前身。
同時,甜水樂團(Sweetwater)聽起來像六〇年代末期的模仿樂團,他們甚至還花時間告訴觀眾他們在來的路上遇到的倒楣事。他們的演出被可愛的老天樂團(For Pete’s Sake)所解救,他們以人聲翻唱器樂曲的方式搭配大鍵琴,詮釋巴莎諾瓦藍調曲風。
有人應該告訴伯特・索默爾(Bert Sommer),他輕柔的嗓音很甜美,但唱出來的時候聽起來像極了困在鐵絲網裡的山羊。寫了經典名曲〈Reason to Believe〉的提姆・哈汀(Tim Hardin)採取了相反策略:大聲高歌,聽起來仍然非常有親和力,雖然走音,但他略帶缺陷的演出堪稱音樂節的高潮之一。
我們才聽到第四片 CD,正經八百的舞台經理約翰・莫里斯(John Morris)就已經開始重複「老掉牙的無聊言論」,告訴觀眾不要爬到鷹架上。扁平的藍色迷幻藥給他更多機會說教:「大家,拜託拜託⋯⋯這是毒藥。已經有 15 個人服用後非常不舒服⋯⋯」
大雨開始傾盆而下。

「朋友們,我們開始今晚的演奏會⋯⋯」拉維・香卡(Ravi Shankar)在1967年的蒙特利流行音樂節(Monterey Pop)令人驚嘆,彼時披頭四受他影響的專輯《比伯軍曹寂寞芳心俱樂部》(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才發行兩週。香卡這次的演出感覺很像重溫過去,但聲音表現卻是目前最好的。多虧這場雨讓電路設置有危害生命的疑慮,所以本來不在演出名單中的梅蘭妮(Melanie)才能帶著她的木吉他上場:〈Close to It All〉與〈Momma Momma〉非常動人,而〈Animal Crackers〉則不但刻意顯得業餘,而且故意唱得粗鄙。我們需要有人振奮我們的精神。

接下來我們聽到,莫里斯想讓不可思議弦樂團(The Incredible String Band)在雨中用幾把木吉他繼續演出的請求,遭到製作人喬伊・波伊德(Joe Boyd)拒絕,也就此向他們原有機會獲得的不朽名聲說掰掰。反而,不知名的阿洛・蓋瑟瑞(Arlo Guthrie)上台,結果出現在電影中,且純粹因為他的和藹友善——他的專輯《Alice’s Restaurant》就賣出了100萬張。
瓊・貝茲(Joan Baez)在週五深夜才出場,時間異常不足,卻透露出胡士托雖然發生在六〇年代結束之前,但儼然已成為一場獻給那個時代的慶典。

1969 年 8 月 16 日,星期六
「讓我們嗨起來!」週六的開場團、很有可能是演出名單上最默默無名的鵝毛筆樂團(Quill)說道。他們也很糟糕。〈They Live The Life〉表演了沉悶的八分鐘,最後以打擊樂方式伴隨諷刺的吟唱:「你好自由!」這場表演在短暫出現的放晴時刻登場,但你大概不會注意到。
舊金山老將鄉村・喬・麥當勞(Country Joe McDonald)表現憂鬱而甜美。山塔那樂團(Santana)流暢優雅的拉丁搖擺節奏大概是整個音樂節上,第一個聽起來不那麼無趣的表演。
正值 21 年華的主唱卡洛斯・山塔那(Carlos Santana)顯然在距離上場還有很長一段時間的空檔時,跟死之華樂團(Grateful Dead)的傑瑞・加西亞(Jerry Garcia)拿了一些麥司卡林致幻劑。多年以後他笑說:「我以為自己有足夠時間等藥效退了再上場表演。」但天不從人願,一切都依照胡士托時間表進行,而山塔那必須提前上場,吉他在卡洛斯手中如蛇一般扭動。但你聽不出來,因為山塔那表現可圈可點。數週之後,他們的〈Evil Ways〉進入熱門金曲前十名。

到了午後,主持人的重心轉移到胰島素與哮喘藥,還有人們遺失的車鑰匙上。
一匙愛樂團(The Lovin’ Spoonful)的約翰・賽巴斯欽(John Sebastian)走上舞台,目瞪口呆。「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這場面有多驚人。你們聚集起來是一整個城市。你們正是我們很多人十年前曾談論過的。」賽巴斯欽接著說自己住在加州的一個帳篷裡,他在那裡遇見一個從事手工紮染的女子——「有愛的話,你只要一間布屋就足夠了。」悠揚的〈Darling Be Home Soon〉是目前我們聽到的唯一一首熱門單曲。賽巴斯欽的表現比任何人都來得好,也許因為他的表演較其他人來得簡短。他表演了〈Younger Generation〉(說是「想把這首歌獻給一個朋友,他老婆剛生完小孩」),而歌詞仍聽起來無比成熟,更甚大衛・鮑伊的〈Kooks〉,這首歌卻是出自這位才二十出頭的男子之手。

「在詢問處有一名三歲小女孩,我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的頭髮是淡金色的⋯⋯」廣播聲伴隨著一陣直升機不間斷地轟隆聲響,之後英國爵士搖滾團基夫・赫特利(Keef Hartley Band)上場,只有一名觀眾鼓掌歡迎。此時,軍隊用直升機將醫療物資送到現場。「他們是跟我們一國的,大家,他們並不跟我們作對!」燈光師兼新主持人奇普・孟克(Chip Monck)在混亂中大喊,值得注意的是,主持人們顯然不再拐彎抹角地説嗑藥的事。

不可思議弦樂團毫無生趣。「哈囉,在我們開始前我要來唸一首詩。」他們聽起來很抱歉,但又有點不爽。他們前一晚本可以為導演麥可・韋德雷(Michael Wadleigh,以胡士托的紀錄片聞名)的攝影機創造出難忘的鏡頭;結果,他們卻排在音樂節常客罐裝熱力樂團(Canned Heat)前面的下午茶時間上場,而且表演的全是新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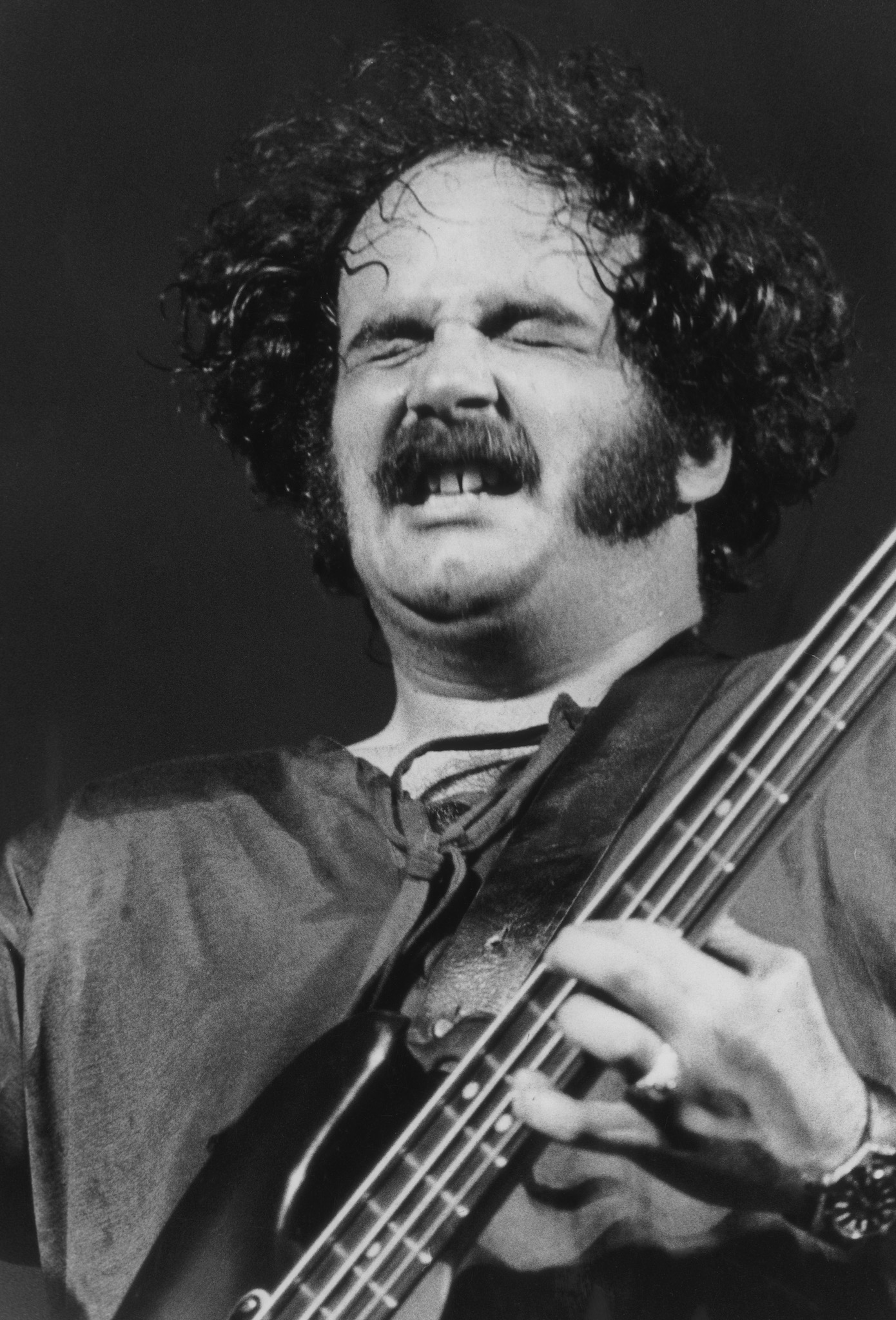

罐裝熱力的狀態無懈可擊,〈Rollin’s Blues〉聽起來像是無產階級版的地下絲絨(The Velvet Underground),而〈Woodstock Boogie〉則像極了美國的現狀樂團(Status Quo),〈Going Up the Country〉後來成了胡士托音樂節的國歌,且在數十年後搖身變為電視廣告愛用歌之一。
山樂團(Mountain)呢?更多野蠻的白人藍調吶喊,更多刺耳的重搖擺節奏。
夜幕低垂,死之華上場了,首先表演〈St. Stephen〉,一首漂亮的歌,以器樂演奏為主,全長大約兩分鐘;接著是鄉村經典〈Mama Tried〉。主唱傑瑞・加西亞像是個未經雕琢的喜劇演員,花了十分鐘說關於「指定停車位」的笑話,同時其他人忙著試音調音。長達 19 分鐘的〈Dark Star〉很迷人,但老天,還真是長得要命。而此次音樂節的主打團,單曲〈Bad Moon Rising〉還在榜上,但可憐的清水樂團(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卻在舞台邊眼巴巴望著時鐘。
1969 年 8 月 17 日,星期日
最後,清水在隔日凌晨登場。在這麼糟糕的時間點上台,他們的表演更加令人讚賞。約翰・佛格堤(John Fogerty)的嗓音很原始但力道十足,〈Born on the Bayou〉跟〈Suzie Q〉兩首歌表現悠長,〈Green River〉簡潔有力但帶有同樣的溫柔感性。清水很帶勁,完全是目前最吸睛的表演。
隨後登場的珍妮絲・賈普林(Janis Joplin)嗓音有時聽起來像極了雷・史蒂芬斯(Ray Stevens)在唱〈Bridget the Midget〉;〈Raise Your Hand〉表現不費吹灰之力,她翻唱比吉斯(Bee Gees)的〈To Love Somebody〉則顯得過度刻意。相形之下,史萊和史東家族樂團(Sly and the Family Stone)極具未來感,跟其他表演者一樣,他們也遇到機器壞掉的問題,但他們「急忙上場表演而不讓觀眾乾等」。砰!直接進入〈Sing a Simple Song〉,表現無懈可擊。幾週前才在榜上奪冠的單曲〈Everyday People〉則成為音樂節又一高潮。

何許人合唱團(The Who)開頭簡直亂無章法,甚至有點慢吞吞。在演唱專輯《Tommy》中的一連串歌曲時慢慢恢復水準;到了〈Amazing Journey〉他們聽起來才有點迷幻節拍(freak-beat)之父的樣子。他們表演途中,一度被國際青年黨(Yippie)創辦人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逮到機會抓住麥克風抱怨:「這全是一團胡鬧,而現在底特律搖滾團 MC5 的經理約翰・辛克萊(John Sinclair)卻在牢裡受苦。」專輯中可以聽見吉他手彼得・湯森(Pete Townshend)大吼:「滾下我的舞台!」但我們無法判斷湯森的吉他是否如傳言所說擊中了霍夫曼的頭。表演最後在音響反饋雜音中不了了之。

傑佛遜飛船(Jefferson Airplane)於日出時分上台,和群眾一起迎接新的一天,一邊解釋自己並非「嬉皮樂團」,而是「狂熱晨光音樂」,接著表演弗雷德・尼爾(Fred Neil)的〈Other Side of This Life〉,慘不忍聽。〈Somebody to Love〉同樣也以極快的速度演唱——但後來證明,這首歌可說是沉悶一天開始前的一瓶能量飲料。

喬・庫克(Joe Cocker)帶著汗水與油膩感演唱巴布・狄倫與雷・查爾斯(Ray Charles)的歌曲,接著另一場暴雨來襲,電力供給斷了好幾小時。
專輯裡將一段雖然短暫但美麗的背景音樂插曲剪了進去。
到了午茶時間,鄉村・喬・麥當勞和樂團重返舞台,表現卻比先前糟糕。 十年後合唱團(Ten Years After)緊接著上場,表演更多雜亂無章的藍調搖滾,然後主持人宣布醫院接收了「一堆斷手斷腳的傷患」。樂隊合唱團(The Band)的表演沉重,人們大失所望,接著演唱頂尖四人組樂團(Four Tops)的熱門老歌〈Loving You Is Sweeter Than Ever〉,輕快節奏扳回一城。接在他們後面的是強尼與埃德加・溫特(Johnny and Edgar Winter)無止盡的即興演奏。
在電影與原聲帶中,搖滾天團血汗淚合唱團(Blood Sweat & Tears)的片段被剪光,顯然是因為他們走音,但你並不會注意到的。他們翻唱蘭迪・紐曼(Randy Newman)的〈Just One Smile〉出奇地動人,雖然可能是有點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作祟的緣故。
1969 年 8 月 18 日,星期一
凌晨三點,克羅斯比、史提爾斯、納許與尼爾楊(Crosby, Stills, Nash & Young,簡稱 CSNY)的演出很溫煦。剛離開赫里斯樂團(The Hollies)的葛瑞翰・納許(Graham Nash)展現藍領階級俱樂部的舞台魅力,大喊:「噢喔,我石門水庫沒關!」接著演唱動人的〈Guinnevere〉。在一連串如淤塞死水的表演之後,他們的現場聽起來就像是一條沒有魚的清澈小溪,清新動人。

到了保羅・巴特菲爾德藍調樂團(Paul Butterfield Blues Band)上場,又回到哀泣豎琴與高頻的白人藍調,不過他們至少還用了首牛鈴主導的勁歌〈Born Under a Bad Sign〉開場。他們讀懂了觀眾的心聲,接下來的〈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是首恰到好處的派對金曲。
快結束了。到了週一的早餐時間,從 CD 上聽起來觀眾人數少了很多。五〇年代復古團沙娜娜(Sha Na Na)聽起來像是二流的秀瓦帝瓦帝樂團(Showaddywaddy)。終於,吉米・罕醉克斯與吉普賽樂團(Jimi Hendrix and Band of Gypsies)—— 或叫吉普賽太陽與彩虹(Gypsy Sun and Rainbows)——開始他們的處女秀,長達兩小時,而且棒透了。

舞台聲音怎麼突然變那麼好?罕醉克斯如往常一樣幽默得不得了,解釋新歌〈Izabella〉是「關於一隻貓,巴拉巴拉,汪汪⋯⋯」他們之後沒能維持這個陣容十分可惜。罕醉克斯不斷重複評論道觀眾的「耐心」,他接著演奏美國國歌,他的吉他在〈Hey Joe〉的最後盡情衝刺,就這樣一切結束。令人訝異地,掌聲很快地靜了下來。
以實況時間聆聽胡士托音樂節,收穫了什麼?宏大沉重的白人藍調搖擺節奏在 1969 年風行全美;相較之下,CSNY 樂團甚或梅蘭妮的靈活技巧,顯然是搖滾樂接下來的走向,即便只是為了精神解脫與壓力釋放。史萊和史東家族樂團是年度最佳新團,創造了新型態的節奏藍調曲風。
你完全料想不到後來會有《花生漫畫》的角色以「Woodstock」命名(一隻小黃鳥,是史奴比的好友,中譯「糊塗塌客」)或是胡士托會成為 1960 年代反主流文化的代名詞(其實 1967 年的蒙特利流行音樂節更適合)。但是此刻我再清楚不過,為何胡士托音樂節的影片與原聲帶令青年時期的我反感。它聽起來根本像一場戰爭,有時候甚至很可怕。當我今年在綠人音樂節(Green Man)大啖喀拉拉鯖魚咖哩時,我會默禱,如果十年後合唱團決定來場突襲表演,我將能夠走回我的民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