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全天候送達的工作電郵,讓許多勞工體驗到前所未有的圍困之感。失聯的權利,法律能否幫上忙?
10 年來,人們都能透過電子郵件找到強納森(Jonathan)。他收到訊息的時間,最早從 6 點開始,最晚直至午夜,持續每天 12 小時。而自他成為律師的那一刻起,人們對他有了明確期待:他會儘可能地,一收到訊息就馬上讀取。
「當你從手機上收到這些電子郵件時,就像我們現在習慣的那樣,來自內在和外在的壓力都很巨大,這股壓力會促使你去做點什麼,」來自西北英格蘭,41 歲的強納森說道。
他皺著眉頭,回想起他在與伴侶度假時,查看了收件匣,因此在一個旅遊景點引發激烈爭執。「他對我說:『你現在看了能做什麼?』我說:『我什麼都做不了,但我必須知道,我必須看看有沒有什麼需要我回覆的。』」
在疫情之前,我們已經得很努力地維持公私界線;對多數人來說,工作往居家環境的遷移,是最後一擊。我們這些遠距工作的人現在工時更長、工作強度更高——而最明顯的徵兆,或許就是管理我們的收件匣,這個薛西弗斯任務(註1)。
去年一份針對來自北美洲、歐洲及中東地區 310 萬位勞工的研究發現,企業內部電郵的平均數量及收件者平均數量,皆有「顯著且持久的增加」。在計算 24 小時內第一封和最後一封寄送郵件(或與會會議)之間的時間後,研究者得出結論:疫情開始後,工作日的工時平均延長了 48.5 分鐘。
27 歲的社群經理凱蒂(Katie)表示,她最晚會在 10 點或 11 點時收到電郵。「遠距工作時,人們會在任何時間點對你盲目地發送電郵,並期待你還醒著能處理——這完全脫節了,」她說道。另一封送至收件匣的電郵發出聲響,將她從晚間的放鬆行程拉了回來,這馬上觸怒了她,讓她關掉了手機和筆電的通知。
「我知道這是因為同事被工作壓得喘不過氣,他們只是想試著在隔天的工作開始積累前,先處理掉一些工作量……但當你在吃飯或看電視時,聽到那一聲『叮』會讓你覺得自己永遠都在工作。」
把通知設為靜音能幫助凱蒂建立界線,她可以自己決定是否要在幾小時後再確認電郵——她承認,她會這樣。「如果你是一個菜鳥,又想證明自己的價值,這真的非常難。」
這就要談到在下班時間接收工作電郵的議題核心。有些人可能會辯稱,不去檢查電郵很容易,但大量不斷地溝通——電郵、簡訊、即時通訊、群聊、來電——僅是表面徵兆。真正的問題更加難以處理:現代職場普遍預期,你應該要即時為雇主效力。
失聯的權利
「早在疫情之前,就確實感受到,數位科技讓工作和家庭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而這種感覺被急速增強了,」展望工會(Prospect)研究主任安德魯.佩克斯(Andrew Pakes)說道。「人們無法休息或關機,這增加了心理壓力。」在英國,展望工會正在推動一項對某些人而言,可能看似激進的收件匣管理方案:政府干預。
它想讓「失聯的權利」在預定於今年下半年推行的就業法改革中獲得認可,避免老闆們在工作以外的時間或員工休假時,例行性聯繫員工。作為保護彈性工作的系列措施之一,英國工黨也表達了支持。
展望工會的提案中,員工數 50 人以上的企業,每年都需要與職員和工會協商,管理下班時間的通訊行為——儘管實際執行會由每位雇主決定。2017 年,法國也有一條類似法案生效,這在全球引起迴響;義大利和西班牙緊隨其後。
疫情不過是增加了人們對失聯權的興致。二月,歐洲議會呼籲,失聯權要成為整個歐盟勞工的基本權利,直指「永遠待命文化」對工作與生活間的平衡造成影響。斯洛伐克今年引入該條法律。4 月,愛爾蘭引入「行為準則」,不僅要求積極參與這個議題,也要求進行檢討、訓練及公正審查。在加拿大,該國政府正在研究一條類似政策;荷蘭政治人物則在準備為此主題進行辯論。
強納森想關掉手機的掙扎,持續造成他的痛苦及伴侶關係緊繃,而這在疫情爆發後只變得更糟——糟到他已在考慮離開法律界。「我知道下一個 30 年不能再這樣下去,」他說。「你必須考慮這是否正確。我很討厭『心理健康』這個詞——但疫情爆發這 15 個月以來,已造成如此顯著的衝擊,人類又會為這付出什麼代價?」
倫敦大學互動中心研究員安娜.魯尼卡(Anna Rudnicka)表示,在辦公室時,我們把來自同事、日常習慣的信號視為理所當然:休息一下、吃午餐和停止工作。「現在,許多人不知道休息一下是否恰當,」她說道。而我們的個人和工作用裝置往往是同一個,以致於我們不知道該如何休息。
工作日的時間延長和強度增加,正導致顯著的健康失衡:尤其是活動不足、睡眠中斷、重複性勞損、壓力、憂鬱、焦慮及過度疲勞。
住在英格蘭中部的 50 歲教師芭芭拉(Barbara)最近為了養病休假一個月,而她仍會收到一些電子郵件,其中寫著只有她能回答的問題,以及請她回來上班的請求。諸如「等你回來時再看!」的郵件標題,對減輕壓力的幫助微乎其微;對芭芭拉而言,她的身體狀況好到足以使用電腦這件事,就代表著會感受到回覆信件的壓力。「我想我應該超前部署,做一點工作,」她說道,語氣聽來極其厭煩,尤其是對她自己。「這就是不會停止。」
芭芭拉說,她 30 年的教職生涯中,實際的工作並沒有太大變化。不同的是對教師的時間要求——從如今擁有專用傳訊平台的家長,到能夠全天候委派工作的校長。
「它連續不斷,真的,」她說道。「它不會考慮家庭生活或停工時間——而這正是它必須改變的地方。」
而她自行安排下班可用時間的嘗試,被她一些同事全天候的回覆破壞了。「有些人不會介意,」芭芭拉說道。「我想那是因為他們從來不知道有其他方式。」
但即便個人界線可以守住,個人要在壓力和過度工作的情況下做出改變,也相當困難。芭芭拉承認,即便在病假期間,快速地看一下收件匣也比放任訊息堆積來得好。「一個月後回去上班,要在 Teams(註2)上挑出數百封訊息,還有其他一切,會花上好幾天,」她筋疲力盡地說道。「這就像,寧可跟熟悉的魔鬼打交道……我真的認為,我們就是自己最大的敵人。」魯尼卡說道。這是我們工作方式的惡性循環,人們感到焦慮、壓力和心煩意亂,然後他們會投注更多心力讓自己能被看見,並以此作為補償。「這創造了一種可用性(availability)的文化:如果你的同事寄了一封電子郵件,你不會想當那個不回覆的人,」她說。
而要如何打破這個文化,就是挑戰所在。下班後收到的每一封電子郵件,都讓勞工陷入兩難:回覆它,然後鼓勵這個不可持續的系統;或是秉持原則拒絕回覆,然後承擔可能的後果。這是真的:疫情前,英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在家上班的人們,與在辦公室上班的人們相比,獲得升遷、培訓或獎金的機率,明顯較少。在 COVID-19 時代,工作不穩定,勞工可能更感到無法拒絕不合理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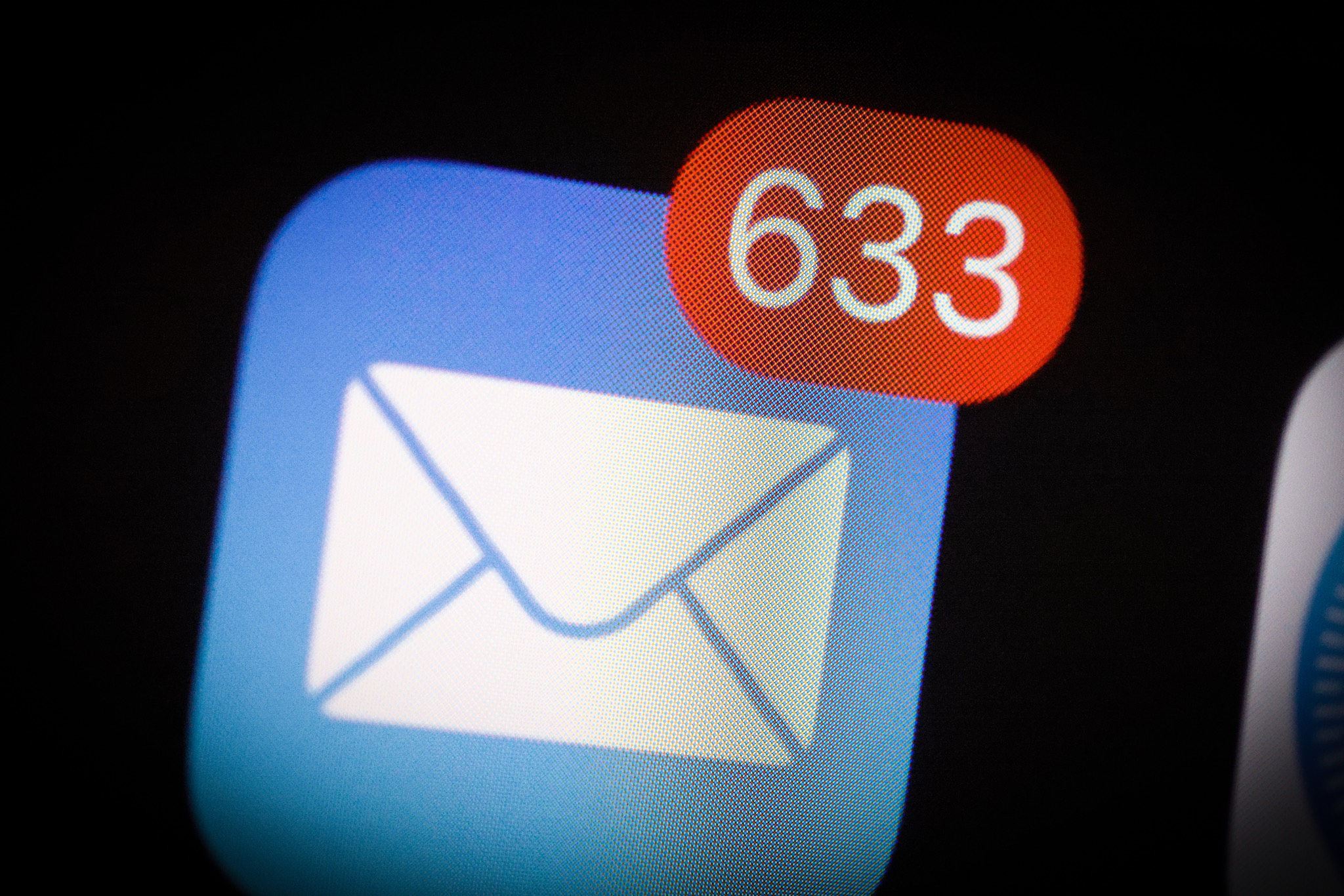
立法與協商之間
貝爾法斯特(Belfast)的 IT 顧問克萊兒.默萊利(Claire Mullaly)最近為了引起大眾對展望工會運動的關注,挺身而出,談論她自己電郵過量的問題。「這不只是老闆有緊急狀況……這不斷在發生,」她說道,聽起來就像被圍困一般。對默萊利而言,這個問題取決於她的工作類型的結構。因為她是為特定專案簽約,她必須要能隨傳隨到,但願自己不會錯過任何機會,而零工經濟的成長,已然剝奪了較長久雇傭關係能帶來的保障。「勞工的力量被削弱了非常多,」她說。但經理人也同樣為此所困。「這就像一個壓力的金字塔結構。」
將工作與生活的平衡視為勞動法問題,能讓勞工及工會發聲,並迫使雇主面對他們的營運現實。「最終,如果人們會在他們下班後例行勞動,我們會需要長期、仔細研究其中原因。」佩克斯說道。
而圍繞著員工需求所製作的日程計畫,這種高度個人化、激進的工作場所組織方式,已經被證實能夠有效減輕過度勞動。但對於如此細膩的改動,立法可能是個太過直截了當的方式。確實,要把失聯權供入廟堂之中,會與為了適應兒童照護、不同時區的同事而建立的廣闊工作樣態有所衝突,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數位創新 KIN 中心助理教授艾拉.哈芙瑪茲(Ella Hafermalz)警告道。
「當你開始禁止人們在特定時間工作(例如,刪掉在下班時段寄出的信件)聽起來像是賦權的倡議做法,可能變得像家長式教條,有損彈性工作本應提供的自主權,」她說。
「我們持續爭取且不願失去這種時間和空間上的彈性。」在過度勞動根深柢固的工作場域,外部干預可能會有所幫助,但更多時候,哈芙瑪茲說,「能夠失聯通常是公司或產業文化的問題。」確實,法國 2017 年「下班離線權」(le droit à la déconnexion)條款生效後,其行政部門的調查顯示,78 % 勞工仍繼續在下班時間讀取工作郵件和文字。
勞動法只會要求企業協商出一份協議,這類文件中,僅 16 % 對其勞動工具和時間有精確的定義,未履行協議的雇主,也不會受到任何制裁,這尤其在疫情期間,促使人們要求闡釋、加強法律。
這表明了,沒有獲得雇主支持的立法有其限制,也代表著一條更即時的改變路徑:直接與雇主協商。
舉例來說,在德國,長期以來,直接與雇主協議失聯權是標準做法。據報導,福斯(Volkswagen)是全球第一家禁止內部郵件在晚間 6 點 15 分到上午 7 點間轉寄至私人帳號的公司。法國電信業巨頭 Orange 則在 2016 年共同勞動合約中,正式承認失聯權。
其他企業也採取了相應措施,包括允許勞工在下班時間關掉手機,或是在假期間停止電郵傳送。自疫情以來,有些雇主給了員工更多的有薪假期,希望能避免過勞情形。約會應用程式 Bumble 所有 700 位員工,獲得一整週時間能夠「全然離線」。
這表明,企業正在認知到工作與生活平衡的重要性——即使只是在它們的底線。創造長久的改變需要承諾和資源,默萊利表示:「好處就是:你會得到快樂、精神煥發,而非不斷跳槽的員工」。長期而言,留任率和工作表現會進步;企業甚至會自我行銷為「擁有失聯權的雇主」以吸引人才,她指出。
但失聯不僅是一項特權,它是「這個新世代最大的健康和安全挑戰之一,」佩克斯說道。即使是在疫情之前的 2019 年,與工作相關的高壓、憂鬱和焦慮行為,造成1,800萬個工作日消失。而其真正的代價,才正要逐漸顯明。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國際勞工組織(ILO)5月發表的一項指標性研究發現,每週工作 55 小時或更長時間的勞工,其罹患中風和致命心臟疾病的風險顯著增加。長工時是1/3職災死亡的原因,而在此之前,這項風險被徹底忽略。
這項數字表明了我們採用目前工作方法的代價,以及現存保護條款的缺點。WHO 及 ILO 已經建議,要有更多法律和集體談判來保護勞工健康,但首先,我們需要接受:工作本身需要改變。
而當遠端工作和混合工作模式開始扎根,時間點變得至關重要。佩克斯建議,在沒有保護的情況下,這可能會帶來「新啄食順序」(new pecking order),勞工的價值取決於他們的可用性,專業職位會被拆解成分散的任務。「我們不想要訂出新型態的不平等和歧視。」
生產力神話的殞落
過去,彈性被呈現為一種紅利,能提供勞工更多的便利性或自主性,卻會在實際上侵蝕工作界線。新堡大學商學院未來工作教授艾比蓋兒.馬克斯(Abigail Marks)說明,儘管眾人皆知人們普遍感到筋疲力竭,疫情期間報導的生產力大躍進仍被譽為居家工作的勝利。「心理上來說,我們不可能繼續這樣工作,」她說道。
未來,我們或許會被迫去探索其他在產出(包括電子郵件)之外的績效表現判准。第一步,馬克斯表示,是我們要「停止這種對於生產力不加修飾的表揚」,同時抵制這種推斷:為此犧牲我們的時間和健康,是值得的。
芭芭拉最近對她的老闆這麼做了。「我說:『我們總是在談論健康和福祉,說它們有多重要,但你卻在昨天晚上 8 點 50 分傳訊息給我。』」他們的關係很好,而老闆對此感到抱歉。「他說:『我只是打了字,我沒想太多』,而這就是問題。」為了以此作為這些對話的後援,她全力支持失聯權在法律中獲得承認。
當每一封信件層層疊加,我們都可以盡自己的一份力。勞工可以藉由結為工會彼此馳援,盡可能不去回應下班時間的通訊。
作為 eWorkLife 計畫的一員,魯尼卡一直在研究遠距工作的有效策略,她表示,改變你的工作電郵簽名檔,標明你的上班時間或可聯繫時段,可以建立一個良好的界線。同樣地,你每天查看工作收件匣的次數限制,也能在必要時上呈給你的老闆,以達到專注目的。
但,魯尼卡補充,管理層必須帶頭,不只是在物質上支持雇員關機、休息,他們自己也要這麼做。「整個企業都要確保,人們要失聯是 OK 的,」她說。這可能代表,給予雇員專用設備,讓他們可以在工時以外時間關機;或採用「電郵規章」,防止人們發送不必要的訊息且預期會得到立即的回覆。
現在已經返回工作崗位的芭芭拉,已在採用倡議作法:將通知設為靜音、排定電子郵件延遲發送,把它們維持在工作時段,並且警告同事,她不會在週末確認郵件。這些可能很快就會成為政策,她說。「要改變的,是人。」
註1:薛西弗斯,希臘神話人物,因為遭到天譴,必須晝夜不休地推著巨石上山,被用以形容永遠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註2:Teams 是微軟 Office 365 旗下的團隊合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