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誼關係不是與伴侶關係同樣好嗎?甚至更好不是嗎?兩個人在一起,日復一日,但不是因為性愛、生理吸引、金錢、孩子或資產而緊扣在一起。」

當家庭開始主導生活,友誼還能保有什麼樣的角色?
有多少人活在朋友的陰影之下,與他們比較自己擁有的親密關係、工作與為母方式?這些是我問過自己的問題,我在將近 40 歲、第二個孩子出生前離婚。我以前總習慣向丈夫尋求幫助,而現在,因為不習慣向朋友求助,所以總感到尷尬畏縮,尤其是當他們有孩子的事要忙時,更會感到自己很累贅。
當我擺脫 30 多歲的動盪狂亂,我問自己以前的友誼還剩下些什麼,並責備自己之前疏於維繫人際關係,往往只是偶爾與朋友見面更新近況,而沒有持續參與彼此的生活。當我生病需要有人來照顧時、亟需睡眠卻需要有人照顧寶寶時,或是當我好幾天都沒跟另一個成年人說話,而需要某個朋友放下家庭一個晚上時,我不知道該聯絡誰。
我懷抱著焦慮,一方面感謝那些陪在身邊的朋友,一方面因為不在場的人感到落寞,便轉向了虛構朋友們的懷抱。我讀著艾琳娜‧斐蘭德(Elena Ferrante)的那不勒斯故事四部曲(L’amica geniale),對於艾琳娜(Lenu)在身為單親媽媽期間,重拾她與莉拉(Lila)的情誼感到高興,好奇她們兩人的友誼為何似乎比婚姻更朝氣蓬勃。對我來說,閱讀好似在交友,縱使我喜愛的作家與實際的朋友同樣令人惱怒,且同樣讓人不安地陌生。
我對於描寫團體的小說尤其著迷。對很多人來說,關於一群好友的影集能讓我們有一種奇特的暫離現實之感,就像加入了一個比真實朋友還要徹頭徹尾地幽默風趣、更溫馨有愛,且更可能天天現身陪你的小圈子裡。看《六人行》、《慾望城市》、《女巫前線》、《美麗心計》、《性愛自修室》(擁有一群青少年朋友這件事讓中年族群感到困惑)等影集時,我們感覺自己也是劇中人物的一分子。
從目前正在讀的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1963 年的劃時代小說《群體》(The Group,暫譯),我也有同樣的發現。這本書是如此令我滿足,卻又不是我心目中典型的千禧年前倫敦世界,因此讓我萌生自己寫一本的念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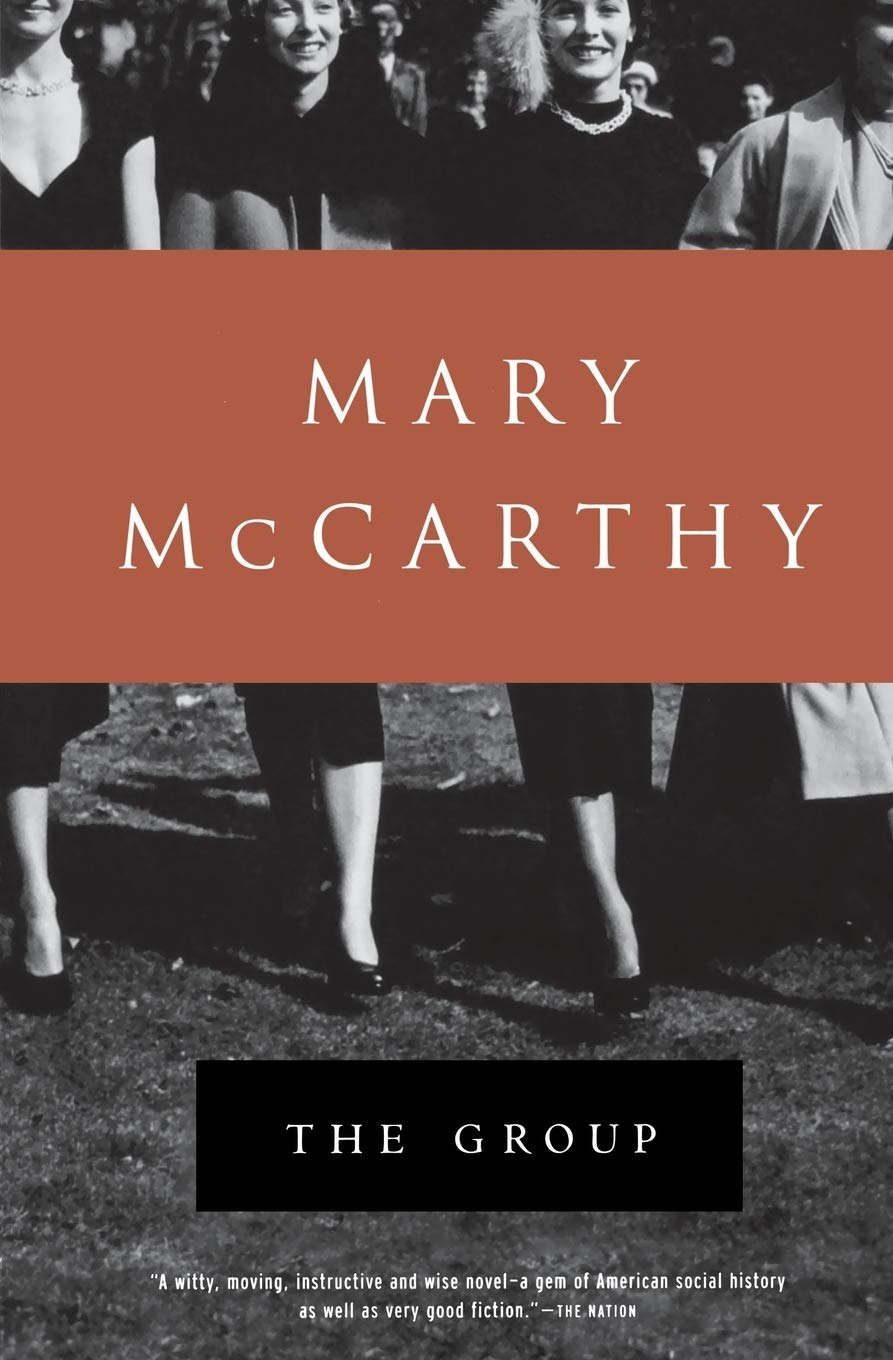
的《The-Group》.jpeg)
我喜歡麥卡錫的小說,因為它兼具民族誌描寫式的距離感與親密性。當她開始寫小說時,已經是個吒叱雜誌圈的時髦人物。她決定試著以散文風格寫小說,在《群體》中記敘了她在菁英女子學院瓦薩學院(Vassar)的日子。她說她對世代間的發展遲滯很有興趣。為什麼那些女人仍舊在做丈夫的僕人,仍舊在假裝自己沒有那麼聰明、隱藏對性的好奇心,仍舊為了母職而放棄事業?她提醒著現代的我們去探問,我們是否直到今日仍不勝其擾?


受到麥卡錫啟發而寫出《慾望城市》的坎蒂絲‧布希奈兒(Candace Bushnell)說:「《群體》提醒我們,很多事其實沒怎麼改變。」1963 年,《群體》書中展現令人訝異的親密關係,至今仍深深感動我。當看到多蒂(Dottie)將童貞給了一個男人迪克,血滴零落在床單上暈染開來(她困惑地想:這樣夠嗎?),並感受到自己第一次高潮的顫抖(「她似乎在一長串難以控制的收縮中爆發,這令她感到尷尬,就像打嗝,當高潮結束,幾乎像她已經忘了迪克這個人一樣」),然後是整個尋求避孕的痛苦過程。
回顧麥卡錫之前的世代,維吉尼亞‧吳爾芙的《波浪》(The Waves)是一部講述團體的出色小說。吳爾芙以如今這個狂亂年代難以得見、卻極吸引人的能量忠於友誼。她和姐姐凡妮莎‧貝爾(Vanessa Bell)及她們的朋友們擺脫家庭生活的專制,建立了一個以友誼為基礎的社群。我獨自抱著嬰兒,羨妒著他們的世界,思及貝爾,她在自己的農舍裡撫養孩子、繪畫、做飯,被朋友和戀人包圍著,儘管我還記得這般場景可能對身處其中的孩子造成混亂。與布魯姆斯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的其他人一樣,吳爾芙對喬治‧愛德華‧摩爾(GE Moore)滿懷感激。這位哲學家所提出的理論是建立在友誼的基礎上的,他認為友誼是「我們所知或所能想像中最有價值的事物。」吳爾芙想用《波浪》見證她所依賴的友誼,也證明人透過與朋友完全契合的關係,可以構成一種「我們無法獨自成為的完整人類的主體」。

她以介於思緒和演說之間的獨白口吻講述她們的故事。六個朋友直接對著我們說話,先是稚嫩的語氣,而後轉趨疲倦。與麥卡錫的小說相比,她的書少了些譏諷和民族誌元素,多的是象徵手法,一個世代如日出日落、潮起潮落般興盛衰敗。「我們順著隻字片語融入對方,」伯納德(Bernard)說道,「我們的稜角罩上一層薄霧,不再分明。」這般交融是友誼所帶來的快樂,但同時也伴隨著恐懼,擔心一旦融入對方以及這個世界後,就可能不再是獨立的個體。
許多優秀的群體小說都涉及其中一個角色的死亡,這或許不是巧合,而是一個機會,讓剩下的朋友審視作為團體一員的自己,同時揭露過去需要被隱藏的真相。在麥卡錫的小說中,一開始結婚的凱(Kay)最後去世了。「我的老天,我以前真是受夠『那群人』了!」她的前夫哈拉爾(Harald)在葬禮上如此談論她的大學同學們。他厭倦的,就如凱自己有時也厭倦的,是她們總是喜歡嫉妒、憐憫和批評他人。他厭倦的,還有那些正面的特質:她們相互扶持的能力。要是沒有她們,凱或許會繼續接受他的情感操縱(gaslight)(註),並在他送眼睛烏青的她到醫院時,吞下他的不實指控,說是自己弄傷的。或許她也會繼續相信,他玩弄感情的作為能因為天性如此而被原諒。
凱的朋友們讓她勇於結束這段婚姻,卻沒能阻止她從窗戶墜樓(或者是跳樓?)。在她入土為安後,她們捫心自問,自己是否應該對她的幸福擔起更多責任。而在《波浪》中,是羅達(Rhoda)的自殺真正讓她的朋友們體認到,群體生活的快樂有多麼危險。你們互相依賴,卻沒有能力讓彼此活下去。另一本講述群體生活、衝擊力十足的小說中也出現了自殺情節——柳原漢雅的《渺小一生》。
註:此詞出自描述這類情感操縱故事的電影《煤氣燈下》(Gaslight,1944)。指情侶關係中一方以謊言操縱、矇騙、精神虐待另一方。

演出《A-Little-Life》舞台劇,改編自柳原漢雅同名小說,四個相識於大學的好朋友,他們畢業之後一起在紐約經歷三十年的人生浮沉。-@ITAense-scaled.jpeg)
《渺小一生》講述四位男性友人(跟麥卡錫的小說設定一樣)因同為大學室友而相識,之後一起搬到紐約生活:有著英俊臉龐的演員威廉(Willem)、任性不羈的畫家傑比(JB)、擔心自己佔盡優勢而不配當黑人的建築師麥坎(Malcolm),還有聰明卻遍體鱗傷的裘德(Jude),他曾遭到身體虐待及性虐待,因其殘疾(他的腿傷帶來極大痛苦)與自殘傾向,朋友們總是想要保護他。的確,很多時候朋友們因快樂而相識,但真正讓我們彼此緊密相依的是痛苦。這本小說正是關於這項發現,也緊扣這段可能會帶來危險卻時而熱絡的親密關係。
在我讀過的小說當中,《渺小一生》將友誼敘寫地最絲絲入扣、強而有力,並不將伴侶關係視為更重要的存在。多數描寫一群好友的小說,會在角色年紀稍長後,將他們分別配對成伴侶。在梅格‧沃里茲(Meg Wolitzer)的《興趣》中,於青少年夏令營相識的一群朋友一起走到了中年。其中,朱爾斯(Jules)很介意「一旦有了小孩,就將朋友踢出陣線」這類將好友情誼轉為家庭間偶爾相聚的狀況。
這個情況在柳原漢雅的小說裡並不成立。她筆下的角色多為男同志,創造出來的世界並不以繁衍為重。一開始,這被視為不成熟。當 20 多歲的裘德和威廉住在一起時,麥坎的父親批評他們長不大。
「為什麼,」威廉感到困惑,「友誼關係不是與伴侶關係同樣好嗎?甚至更好不是嗎?兩個人在一起,日復一日,但不是因為性愛、生理吸引、金錢、孩子或資產緊扣在一起。」而沃里茲筆下的角色也挑戰友誼的定義,讓「朋友」一詞比往常承載更多的可能性。裘德發現「朋友包含了許多層面,但現在包含太多了。」柳原漢雅的角色則實踐了這樣的包容性。
《渺小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刻,在於威廉發現麥坎的父親是對的,他們過去三十年來似乎太放縱於這場「延長的睡衣派對」,這項體認讓他有種「逃過大劫的顫慄感」,因為他們找到了另一種替代的生活方式。
距離我開始如此迫切地閱讀關於團體友誼的小說,已經有好幾年。我的女兒即將滿3歲,屬於我自己的群體小說剛剛誕生。但我在封城期間又回頭想起這些小說,想到我們分別回到自己的家中後,將會如何擱置這些不穩定的需求與責任。疫情期間,我們被告知對朋友最負責任的方式,就是遠離他們,這點實在很難。我擔心在朋友圈中,只有我在思考這或許不是避免受苦的最好方式。在過去幾個禮拜中,我十分介意朋友們退居各自的家庭生活泡泡,同時也擔憂那些比起充滿病毒的外在世界,在家中得面臨更多肢體暴力危險的女人們。
我退守到了由兩個家户所組成的非核心家庭,有兩個孩子穿梭其間。我目前與新伴侶同居,在很多層面都是一種解脫。再次地可以在安全的兩人關係裡避難,在這裡,能假定彼此互相需要,且能遠離令人困惑的、不平衡的友誼關係。知道身旁有個人可以在你需要時逗你笑、陪你思考或哭泣,是件令人高興的事。
但我不禁想,《波浪》中的角色,或是麥卡錫描寫的女人們,抑或是柳原筆下的男人們,會如何面對這個時代,他們會找到更團結一致度過的方法嗎?我希望我們現在不要害怕彼此的細菌,害怕被彼此的身心所污染。我希望這個時代會出現新的友誼形式,並有新的小說來刻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