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計,東西的誕生
Access to Tools 靠近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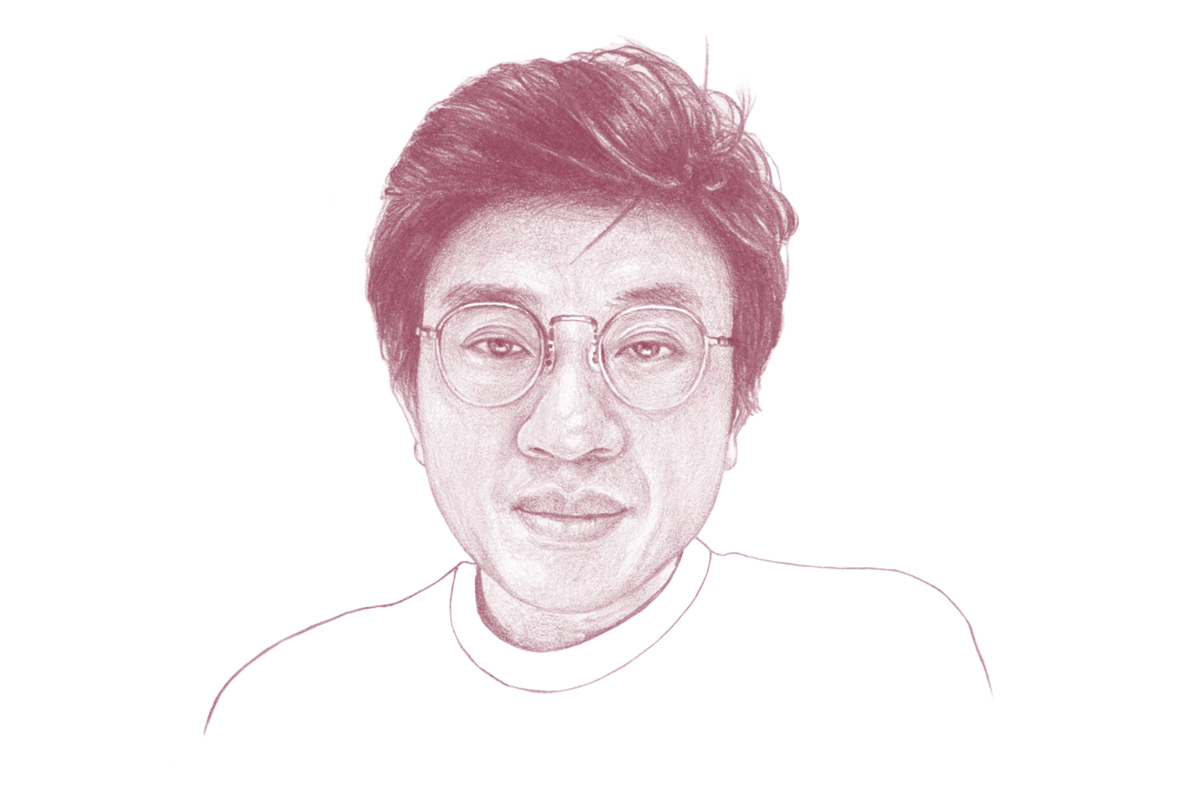
上週實踐工設的大學生舉辦期末作品展演,邀約台北設計之都前執行長吳漢中與我對談,年輕的未來設計師預先提出了熱情的提問:「設計如何改變社會!」接到這題目,我心想「設計能夠改變社會嗎?」就算可以,「設計需要去改變社會嗎?」從研究社會的學術機構大膽轉軌到設計學院教書的我,經過兩年多教學現場的現實校正,答案還會是肯定的嗎?坦白說,我的直覺仍舊沒有改變,雖然詳細的理由尚不清晰。這會奇怪嗎?一點也不,因為人們從來都不需要絕對保證才敢賭注於改變,需要的只是「合理的希望」(Reasonable Ho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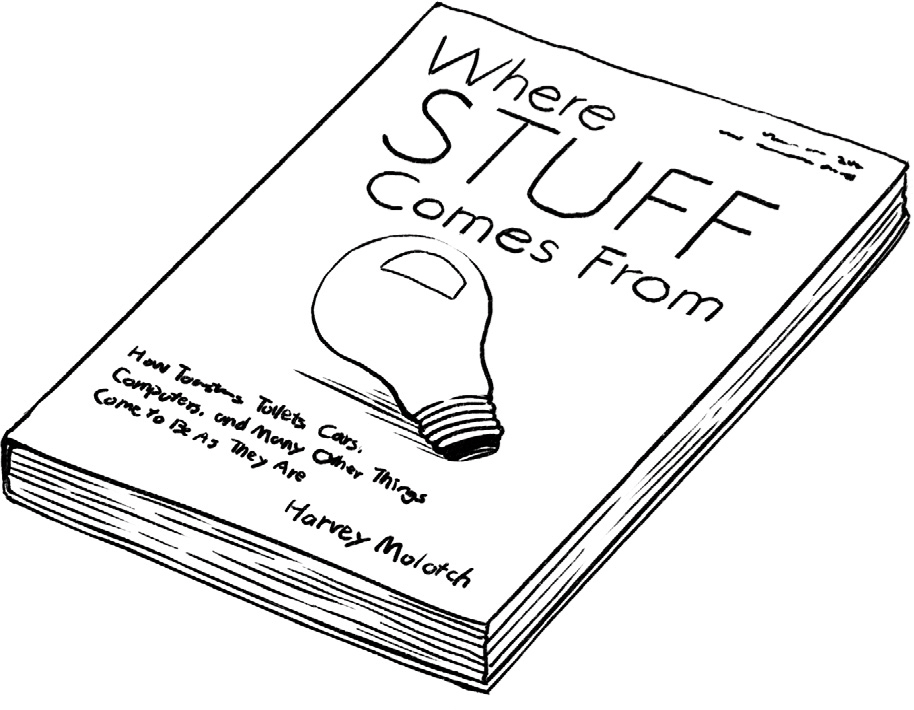
談到「改變」(change),很多人會聯想到美國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以及他那句「Yes, We Can!」的競選口號,事情確實有了改變,但不是他希望的方向。2017 年,美國新政局讓當年的口號變得嘲諷,川普主政後美國社會經歷眾多始料未及的重大改變,諸多被(現在我們知道)輕率地認為進步運動不可逆轉的文明成就一一被新的改變所背叛。美國之外的「改變弔詭」也不遑多讓,還記得 2011 年由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開啟的「阿拉伯之春」嗎?一度被認為「第四波民主化」的樂觀改變已成了挫敗的苦難,反而啟蒙的歐洲文明在大量難民湧入下正承受著社會解組的莫大危機。當然還有台灣自己的太陽花運動,最近的勞基法修法爭議讓許多人義憤填膺,認為是又一次逆向倒退的改變。
2012 年電影《女朋友。男朋友》裡有句讓人印象深刻的台詞:「妳不要怕,明天一醒來,台灣就不一樣了。」六年後我們醒來,楊雅喆導演給了我們關於「無愛的未來」的《血觀音》,黃信堯導演則給了我們笑中帶淚的《大佛普拉斯》,這是我們必須學著面對的令人頓挫的時代氛圍。單單「改變」已無從引發興奮,許多人現在害怕的反而是「明天一醒來,台灣萬一又不一樣了。」無論是「社會主義」的「大有為國家」,或「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這些抽象而高遠的權力,總是在徵召我們的熱情後,丟下我們陷入「改變」與「反改變」的永劫輪迴。
我不清楚是否有可能跳脫這一切,但我知道,它必然是一種讓權力回歸到凡俗個體手中、沉澱到感官所及的範圍內,為日常培力(empower)的踏實改變,而這不正是「設計」的守備範圍嗎?「設計能夠改變社會嗎?」榔頭、地圖、推車、手機無一不改變了世界的面貌,事實上,舊石器時代的敲製石器催生了現代人的祖先,連人類本身也是設計的產物。然後重要的問題來了:「設計需要去改變社會嗎?」當然!這正是我離開學術高塔「向設計轉向」直覺成理的希望啊——相信「向社會轉向」的設計會是通向未來的新出路。
長年在紐約大學社會學系任教的哈維·莫洛奇(Harvey Molotch)教授是我的前輩先行者,若無他 2003 年出版的《東西的誕生》(Where Stuff Comes From)給我的鼓舞,讓我從社會學的思想叢林裡隱約看到一條人煙稀少、通向「設計所在社會」的蜿蜒小徑,我大概不可能在幾年後成為跟學生笑談「設計與社會共同未來」的社會學家。該書出版之際,我剛升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正回頭檢討為自己規劃長期研究的方向。從博士論文的國際運動鞋採購市場開始,回國後經歷過數個產業研究的累積,關心的社會學課題固然有所不同,但靜思之下赫然發現都與設計相關,物件也都扮演著因果解釋的關鍵角色。這些反思引領著我最後下定決心,將研究生涯賭在「設計」與「物件」上。
糟糕的意外是,一旦開始認真搜集研究文獻後馬上碰到了大麻煩,幾乎找不到任何「認真對待設計」的社會學文獻!莫洛奇教授《東西的誕生》這本奇書簡直如荒漠中遇著甘泉,早在我「設計轉向」的啟程處等著我, 沒有先行者豎立標竿的優異社會學研究當作晨昏對話的心靈夥伴,或許我早將「社會跨設計」(Design x Society)的願景當成不切實際的幻覺退陣下場。時光荏苒,轉眼間我在實踐設計學院擔任教職也已一段時日,有了在設計教室的教學田野中提煉社會學的新體驗,如今對媒合社會學與設計也有了更篤定的體會,所以 2017 年我回頭找了群學出版社,幫老朋友協力規劃 Socio-Design 的系列,第一棒上場的自然是莫洛奇教授這本精采萬分的設計社會學力作,召喚新血加入絕沒有藏私的理由。
莫洛奇教授是在都市社會學、環境社會學、災難與媒體研究等領域都曾經做出創新貢獻的知名社會學者,尤其是 1987 年出版的《都市財富》(Urban Fortune)分析都市地產的金權網絡如何在都市地景的塑造上發揮關鍵的角色。《東西的誕生》一出版旋即在次年獲得社會學圖書獎項 Mirra Komarovsky 獎的推薦,從原本金權城市政經網絡的社會學分析,一下跳到香水口紅、土司麵包機、公共廁所這些小尺度(petite)的設計風景,堂堂一位大教授中年搞起文青風情,轉換不可謂不大。如果你以為這是他偶爾為之的小品之作,那就錯了。莫洛奇教授在《東西的誕生》出版之後,2010 年與蘿拉·諾倫(Laura Noren)合編了《馬桶:公共休息室與分享政治》,接著又於 2012 年出版了檢討公共場所監視器的《質疑安全:我們如何在機場、地鐵與其他模糊危險地點走錯了路》。從莫洛奇教授已經成形的出版,可以看出《東西的誕生》並非意外的插花之作,而是他立意經營「設計社會學」的重要起點。
《東西的誕生》始終並未在社會學界造成太大的影響,與他早年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切入金權城市的大受歡迎對比強烈,這個結果完全在意料之中。原本對資本主義敏感批判的左翼社會學者竟然熱情擁抱起設計!這本專書如果被社會學圈推崇群起追隨那才令人意外。莫洛奇教授清楚自己將會遇著社會學讀者的慣性抵抗,並針對這些必然質疑的回應早就預示在本書內文的重要關節。
這本書的序言〈我從哪裡來〉非常簡短,從「我」到「東西」,人與物平等對稱的格式呼應著英文原書名的「東西從哪裡來」,自省與交心的意味濃厚,甚至帶著內行人才嗅聞得到的動人感傷。從 1960 年代的左派憤青轉到肯認被年輕時的自己不屑的設計,他反思來時路交代了一番心情:「現在,我認為譴責民用品的那股勁頭是低劣的政治策略,就智識而言,也太過迂腐幼稚。」
莫洛奇的生父經營汽車零售,母親家族則是做電器生意,雙親都是商人的家庭傳統給了他成長的重要支援,金錢的奧援他心知肚明,但精神洞見的啟蒙或許要到他年齡見識漸長,準備好書寫這本書時才豁然開朗吧?帶著懺悔的口吻,莫洛奇在書中寫道:「那些哺育過我的手曾被我反咬一口,被我的嘴,也被我的腦反咬。」對他而言,思考設計的社會學意義是脫離同溫層的契機,「本書試圖徹底解開『東西從哪裡來』這個問題,而且我希望解開的方式能跳出自己生命歷程裡的緊張,引導出未來的一些新路向。」
相信設計物可以是社會進步的助力,很難不被社會學的「同行常識」認定愚蠢犯了化約論,主張資本主義商品可以是消費者精神自由的媒介,更鐵定是中了商人行銷伎倆操縱「商品拜物」的毒。年輕時的莫洛奇也是帶著這樣的腦,重重反咬了父母一口。
本書第一章〈接合物:好與壞〉以及總結的第八章〈道德規則〉,頭尾一貫都以直言檢討這種「資本主義批判」的制式論調破題,要社會學者戒掉「對別人的東西說三道四」的壞毛病。這樣直白的書寫有方便讀者的好處,不投緣的死硬派很快就會反感掉頭省得浪費時間,而那些早覺得「哪裡不對勁」的讀者可以熱身,準備拋棄成見,用開放的精神,遊歷莫洛奇教授精心安排的物件身世之旅。
時光回轉到更早,想想這一切轉機萌芽之際,要是我自己沒有「社會學需要好好研究設計」的念頭,大概也不會出現跟《東西的誕生》的邂逅。年輕的台灣社會學者「我從哪裡來」的動機線索,平行於莫洛奇教授的反思,或許可以提供台灣讀者一些在地脈絡的想像,給還在設計與社會的門檻旁猶豫跨界動機的朋友參考。
一、回到發展的原點:
發展社會學是戰後台灣社會學與國際接軌的一個重要領域,當年在現代化理論與依賴理論的爭辯中,台灣找到「東亞四小龍」的學術定位,也受到國際社會學圈的青睞。如今世局已然大變,「發展社會學」更早隨冷戰背景結束而消失匿跡。但生態、永續、食安、能源、老化、安全、人權等眾多問題並未消失,反而在大論述解體失靈之後,從分散、去中心和貼近在地的社會創新與制度實驗下手,成為有識之士關注人類社會未來發展契機的焦點。
設計(無關商業或公共)本質出發點都在解決問題,它的重心不在高遠的法規政策,而是在貼近人身體五感所及的日常場域中,透過力求準確的環境調配來驅動社會實作的改變,進而達到社區與生活改善的目標。社會學如果不能有效連結設計,等於斷絕了社會變革最終要被落實檢視的「最後一哩」。凝視人們與物件交接物質日常中的苦與樂,回到當初踏入發展社會學的初心,「更好的社會生活」需要的,是如莫洛奇的概念所言,「接合」(lash up)可見不可見的事物網絡,讓「東西」得以穩定存在的努力。證諸過去社會學前述突破巢臼的創新創業,沒有比「重新帶回物件」(bringing the objects back in)的設計社會學更適合提供這樣的改革洞見了!
二、產業升級的出路:
台灣社會學圈在面對產業轉型的課題時廣泛預設著對「新興高科技產業」的偏好,半導體、液晶面板、奈米、生技產業逐級而上,充滿著後進國對掉入「落後」、「脫隊」不進則退的焦慮。過去大抵上社會學研究對於傳產殘留的興趣主要擺在探究生產分工網絡的彈性,勞動體制如何壓抑勞動,還有台商如何在外移地連結政商治理的課題。儘管產業結構上更接近義大利中小型家族企業主導的體制,但透過設計加值擺脫代工,從而走上魅力品牌的「義大利式」產業升級之路,幾乎沒有社會學者深入探討,新舊產業交替的「升級」這種社會學者自己最喜歡批評的「線性想像」可能暗中作祟。
我衷心希望莫洛奇這本書可以幫助我們移除,不管是因為「硬派理性思維」(非常符合「代工體制」對技術、成本與紀律的崇拜)或者因為對「資本主義的不信」,無法正面直視「設計」中藝術與感性創意的障礙。弔詭的是,比起「兩兆三星」這類產業扶植計畫在水電、交通、土地等公共建設與租稅補貼政策偏好上向大型企業傾斜、甚至排擠到其他社會部門的弊害與風險,用設計加值產品創意與品牌魅力的產業願景,反而更容易讓產業與社區結合,更適合多元分散的社會民主,也是更加「社會學友善」的路徑,不是嗎?
三、進入造物的倫理:
社會學消費理論經常導向人們在商品消費中異化與消耗反抗意志的結論,但證諸現實,消費抵制與抗爭普世存在於當代重要的社會爭議與運動,設計物的消費者在面對商品價值時,顯然有著超出功利主義的認知框架,道德不安與倫理信念伸張同樣驅動著當代的消費者。他們在網路與現實世界中積極串連、評價、監督、牽制著企業的種種商品設計與行銷。「消費社會」從歷史舞台上現身,帶給企業與社會的最大挑戰,反而是如何跟使用者進行「不被看穿陳腔濫調」的對話,甚至如何透過設計物件的媒介,培力積極消費者(active consumers)參與更大範圍的社會變革。
《東西的誕生》中提及了許多包括 Patagonia 等品牌對於環境生態改善等公共目標的價值訴求,事實上像 Apple 與 Nike 那樣被抗議團體批評得體無完膚的品牌,最終引導他們往上游改善設計製造流程的壓力主要還是來自品牌愛用者,消費者用購買與使用行為公開與品牌「簽下」這些公司必須履行的價值承諾,當然也有權給這些品牌退場壓力。
我們當然更不該忽略,「公平交易組織」與「綠色和平」這類公益倡議團體本身正是大量運用設計手段來傳遞、動員、累積運動能量的高手!就如莫洛奇教授所言,跟他們抗議的對象一樣,同樣也需要透過設計策略與設計物件「說故事」以創造出「為善的時尚」!
「好設計」一直是設計師專業自省的持續發問,從改善個人生活、友善環境生態、降低災難衝擊,到促進社會溝通與避免歧視;從早期工藝美術運動與包浩斯的淑世理想,到近年商業、非商業的許多「社會設計」的案例,不只設計可以從社會學處得到助力更開闊準確地理解如何「接合」物件到真實世界,連結設計思考與實作的社會學可以期待更「唯物地」接近消費生活,以及公民更真實的倫理處境。
第四,攜手設計回到實踐:
設計是一門「實作的知識」,設計學院裡包含了許多從提案到創作,從身體實作的體悟中求知學藝的課程安排環環相扣。但從中研院「純學術」的經院高塔看下來,設計學院甚至搆不上「知識生產」的末班,頂多只是高階抽象知識下滲到低階實作的知識應用。刻板化的扭曲想像將「動腦的知識」與「動手的實作」切割成兩個涇渭分明的世界,於是「說的人」真以為可以思想指導「做的人」,「做的人」私下則暗自訕笑「說的人」只會出一張嘴;「說」與「做」的巨大鴻溝不正是台灣方方面面挑戰轉型失敗的悲劇表徵嗎?
傳統學門分立的專業堡壘無法有效回應時代的劇變,這在先進國家裡早被看得清楚,新的體認如今致力於打破傳統的二分框架,思考姿態要保持在貼近實踐的現場,發問的奧義不在正確與否,而在能否有效引導更開放的探索。知識自始至終不脫人類在特定時空下解決問題的實作產物,是人類與時俱進探索環境、持續演化的創新證據,這是杜威(Dewey)等實用主義者早就提出的「設計思考」。
攜手設計有助於社會學克服危機,重拾實踐精神。近年來歐美社會學與設計圈頻繁交流,跨領域知識實驗已是方興未艾的現在進行式,從「實踐社會學」(practical sociology)、「創作式方法」(inventive method)、「拉闊社會學」(live sociology)等概念無非都反映了透過「社會跨設計」探索社會學創新可能性的最新知識「時尚」。沒錯,正是「時尚」!就像《東西的誕生》終章最後一段,莫洛奇引用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有魅力的馬克思主義」對時尚本質的看穿,是一種拒絕再套穿「社會學」與「設計」涇渭分明「呆板制服」的反命題。
鄭陸霖/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學系專任教師、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