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軟糖
The Things of Ember 物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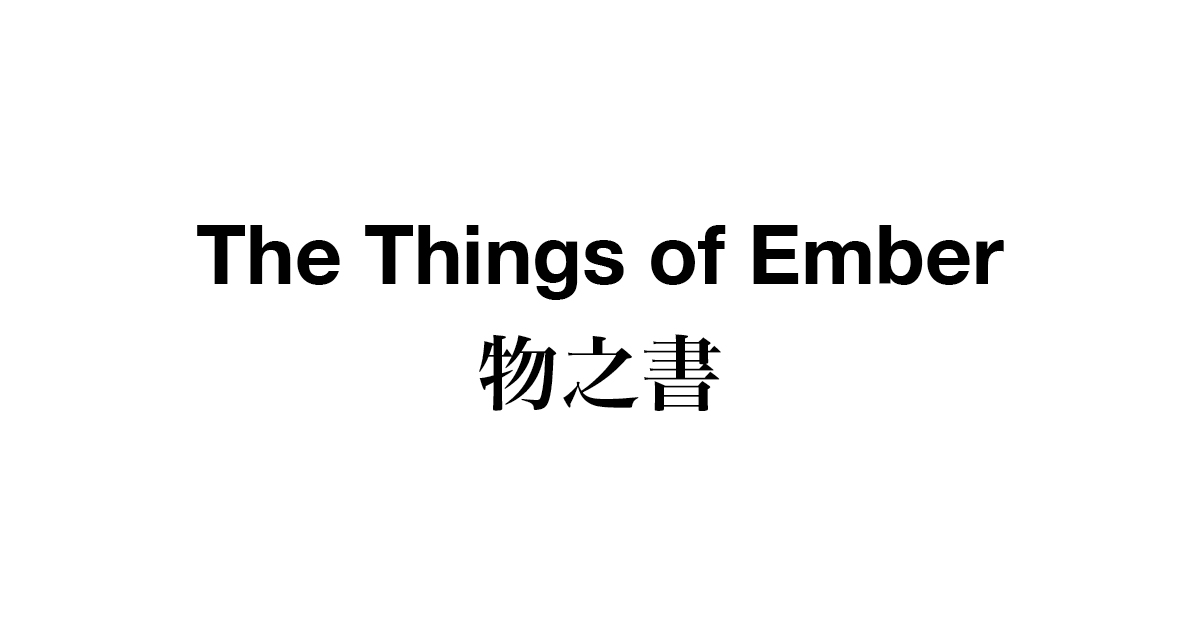
我給她的信裡,提到二十多年前,我在部隊受訓,有一次我們一個班,在一條戰壕坑道裡,我忘了那是打靶實彈射擊,我們是作為驗靶的任務兵;還是那就是一個壕溝戰的訓練?我們全副武裝,戴著鋼盔、拿著步槍、S 腰帶掛著鋁水壺、刺刀、彈匣、摺疊板凳。所有的士兵都跨坐在那壕溝裡,班長還發菸遞給我們。那條壕溝在一片荒枯的草原上,遠遠的槍擊聲像摔破瓶罐那樣,隔許久響一陣。當時我拿著一本小筆記寫信給她。我問她記不記得那一陣子我瘋狂的寫信給她?其實她不是我女友,但那時所有宿舍上下床鋪的,像囚犯一樣發出臭味的士兵們,全瘋狂的寫信給他們能想到有關連的女孩。期待她們即使隨便一封回信,最好信封被附寄一張這女孩的照片,那似乎使這個寫信並收信的人,不是人間失格者,不是絕對孤獨者。
我問她記不記得她寄了什麼給我?
不記得了。
我告訴她,她在信封裡附了一個那種裝維他命的真空小包,裡頭放了一顆粉紅色的棉花軟糖,像小指第一截指頭那樣大小。她在信上寫著:「這是我的吻。你可以在最苦的時候,把它放進嘴裡融化,或是一直收藏它喔。」
她傳了一個圖案,一隻卡通小狗把手塞進嘴裡,一臉驚嚇的表情。她回了一句:那時你是把它吃了?或是一直收藏?
我想描述的那個「吻」,像是宇宙風爐最裡頭那朵冉冉搖晃的火苗。我年輕時和一群人渣鬼混,他們告訴我每一百盒檳榔裡會不小心吃到一顆「檳榔王」,那一吃到立刻就流鼻血,心跳加快,頭冒冷汗,甚是暈倒。這個傳說後來變成每一條黃長壽裡,會有一根「菸王」,像是製菸廠的工人在和他不認識的未來抽到這跟菸的人打一種密碼。告訴我這祕密的哥們,發誓他曾抽到過那根菸中極品,那真是「曾經滄海難為水啊」,抽過那根好像你靈魂都一起白煙裊裊的菸王、菸神,再抽旁邊那些它的菸兄弟,簡直就像抽大便。
是以之故,我想,我們都是一隻隻從印模裡打鑄出來的機器人(像孟山都的基因改造種子?),這些在宇宙時空漂流的辰光,我們只是一些銅汞銀金的金屬盔甲、身軀。除非像煉金術之火,其中一只機器人像抽到菸王的小混混那麼幸運,被這樣的吻,宇宙風爐裡那朵忽熄忽亮的靈魂火苗,送進嘴裡。啊那就是一隻不再孤獨、悲傷的,往宇宙擴張邊際漂浮的機器人啊。
我想你一定認為,我想像灌蟋蟀的老手,往那空無一物的孔洞裡灌水,讓它裡頭鑽出靈跳閃爍的意象蟋蟀。吻?那不就是大腦興奮區,對於近距離的視覺、嗅覺、觸覺的綜合資訊,大量分泌腦啡造成的興奮與愉悅?一張美麗女人的臉,漂亮的鼻子和朱唇,她允許你將舌頭放進那銷魂的、窄小濕潤的嘴洞裡,她的小舌頭怯憐憐輕跳著撩你的舌沿,互相吸吮著。
我想要說的是,其實,很多年前的那個壕溝裡、那片原野的上方突然雷電交閃,大約在三分鐘內天光突然黯晦,然後下起暴雨。我們這些菜鳥士兵全被分不清是天上倒下的雨,或是從壕溝上方流水的積水,淋成落湯雞。我聽到大家一個隔著一個哀嚎著,但班長沒有要收隊的意思。我們也不知道在地面上遠遠那一頭,趴伏在土丘上持槍射擊的打靶隊,是被帶隊回營,還是趴在泥流裡繼續射擊。我分不清楚那在頭頂炸裂的啪啪聲響,除了雷擊還有其它的響聲。當時我將褲子口袋裡那只小密封袋掏出,在一片上下四方的水流中,將裡頭的那顆小棉花糖,濕黏黏放進嘴裡。那一瞬我感到這個女孩用嘴貼住我的嘴,像人們說的那被封印在鴨肉凍裡,那野鴨死亡之前拍打翅翼的鮮活番馥,在舌蕾融化時,細細沸跳的湧現,我的臉上除了鋼盔沿垂流的雨水,還有幸福的眼淚,那個吻像廣島原子彈蕈爆被收進了上帝的一個噓聲嘬起的嘴喙。它整個重現了我為何一身滑稽軍事裝備、濕淋淋站在這水溝裡,那最初的活著的美麗盼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