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客廳沙發就能環遊世界,甚至到外太空或深海底,來場浪漫的約會之夜。在元宇宙裡,愛情比想像中更近
我和 CC 第一次約會時,我們在一個懸浮於遙遠銀河系中央的浮動平台上相遇。CC(他要求我這樣叫他)應該是一隻兔子,但在我看來,CC 就像一個穿著帽 T、有著巨大貓耳朵和尾巴的動漫少女。與許多太空旅行一樣,我們遇到了一些技術難題,原先自在的談話節奏因為我的聲音發生延遲而中斷。有幾分鐘,我的化身(一個穿著短版羽絨夾克和緊身褲的瘦長金髮女人)半蹲著爬來爬去,就像一隻正在找合適角落撒尿的㹴犬。
「對不起。」在我說出道歉幾秒鐘後,我才聽到自己剛剛說話的聲音。「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不需要道歉!」CC 說。他向我保證以前曾見過更怪的事。這就是虛擬實境互動的本質。
約會前一週,我在 Nevermet上與 CC 配對成功。Nevermet 是愈來愈多的 VR(Virtual Reality ,虛擬實境)約會服務之一,用戶可以與其他 VR 愛好者配對,並在元宇宙的某處相約見面;Flirtual 這款應用程式則承諾用戶能「在 VR 中體驗安全又如夢似幻的約會」;還有線上虛擬互動遊戲「第二人生」推出的「寂寞芳心約會機構」(Lonely Hearts Dating Agency)。就連已推出 Tinder、OkCupid、Match 和 Hinge 等交友軟體的公司 Match Group,也在去年11月宣布將推出 Single Town,一處單身人士可以見面並安排數位約會的虛擬空間。
虛擬約會大爆炸
只要一副電量充足的耳機和一顆開放的心就能參加 VR 約會,你和你的同伴可以在 VRChat 中的寧靜灣享受永無止境的海灘日落,或者在「和命運賽跑」(Race Against Fate)中漫步於世界末日後的場景中。你可以在一個有魔法移動牆壁的世界裡玩鬼抓人,或者在被巨大外星水母包圍的水下洞穴中談情說愛。你也可以只和對方相約在酒吧,我聽說這是個流行的 VR 約會選項。
Nevermet 在今年情人節問世,它的目標很簡單:徹底重新設定人性。「我們打算改變約會市場,將外表從人們互相吸引的主因,轉變為眾多因素之一而已。」Nevermet 執行長卡姆・馬倫(Cam Mullen)在電話中告訴我。馬倫認為,現在約會太注重外表了。在虛擬實境中,人類終於可以超越表象,在更深的層次上相互連結,從心到靈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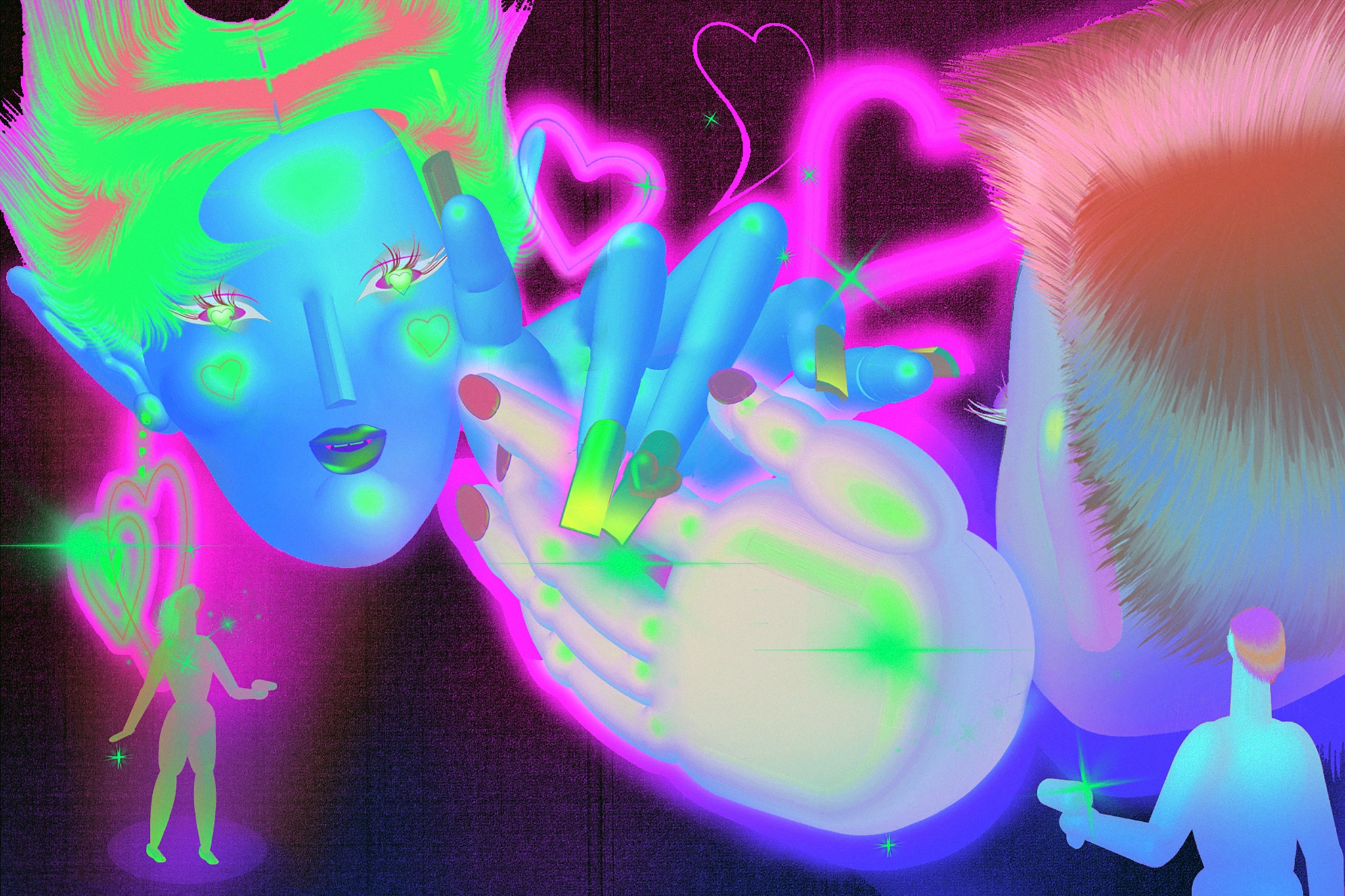
Nevermet 的介面與 Tinder 或 Bumble 等其他交友軟體的介面頗為相似,但用戶的個人資料頁顯示的不是自己在朋友婚禮上露齒而笑的照片,或是捕獲一尾銀花鱸魚時的勝利留影,而是用戶的虛擬化身。用戶通常不會在簡介中說他們正在尋找「冒險夥伴」,而是寫下他們的 VRChat 和 Discord 用戶名稱,以及他們最喜歡的 VR 遊戲。
甚至在精明的開發人員開始為元宇宙推出應用程式之前,元宇宙裡頭就已經有個蓬勃發展的社交圈了,我聽說這個圈子通常充滿戲劇性、詭計、酗酒和 ERP(erotic role play,指色情角色扮演,本質上就是虛擬性愛)。
與我交談過的 VR 常客描述了元宇宙的朋友圈,經常是一連串錯綜複雜的浪漫緊張關係,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在互相勾搭。還有 VR 俱樂部,人們常去那裡喝酒和參加派對。
根據一名女子描述,她在一場 VR 俱樂部的 DJ 活動中,看到虛擬人物昏倒在 VR 地板上,大概是因為操控者在家裡狂歡過頭了。
「這有點糟,因為我認為人們沒有意識到,即便你理論上在虛擬世界裡並不孤單,但現實生活中,你確實是孤單一人。」她說。
有很多人會在俱樂部跟別人上床,這種暴露狂的行徑遭受部分人的鄙視。在一部討論 ERP 優點的 YouTube 影片中(優點:比色情片更身歷其境;缺點:不如真實的性愛),一位接受主持人採訪的 VR 用戶表示,只要不在公共的 VRChat 空間進行虛擬性愛,良心就不會受到譴責。
從虛擬走入現實
「這個圈子非常小。」23 歲的斯托尼・布魯(Stonie Blue)在談到 VR 約會圈時表示。「就像高中那種戲劇性的生活,但角色是一群早就高中畢業的人。」
布魯在 VR 中遇到了他 27 歲的妻子伊蓮・卡拉皮蒂安(Elaine Karapetian);兩人都是 VRChat 的創作者。他們最初因為對樂團 100 gecs 的熱愛而結緣,並在布魯幫助卡拉皮蒂安度過一連串情感糾葛的過程中愈走愈近。正如布魯所說:「事實證明,她戀愛問題的解方就是換個男孩,而那個男孩就是我。」
但沒過多久,布魯和卡拉皮蒂安就面臨了一個現實問題:VR 約會最大的優點在於你可以結識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這同時也是它的缺點之一——當他們相遇時,布魯住在英國的新堡,卡拉皮蒂安住在美國威斯康辛州。儘管他們在 VR 中花了很多時間相處,但對他們而言,重要的是盡快在現實中相見,看看彼此是否真的適合,並進一步認真交往。
2021年5月,卡拉皮蒂安飛往英國,幸運的是,一切順利。接下來,這對情侶又發現了 VR 約會的另一個大缺點:在 VR 中約會可能感覺會很接近現實,但兩者就是不一樣。
「一旦你真的見到他之後,VR 就不管用了。」布魯說。在卡拉皮蒂安離開英國後,他們第一次在 VR 中相聚時一片愁雲慘霧。「因為太傷心,我們一起哭了。這讓人感覺很痛苦,我不想在虛擬世界裡。」
見面後不到一年,布魯去美國旅行並和卡拉皮蒂安結婚了。現在,卡拉皮蒂安正在等待她的簽證並移居英國。卡拉皮蒂安說,即使在現實生活中共度時光對他們來說非常重要,她也知道很多人寧可將他們的 VR 約會體驗完全留在網路世界。
「我所認識在 VR 中約會的人,許多人似乎從未見過面,或者只在遊戲中維持關係。」
馬倫在 Nevermet 上表示,儘管大多數用戶會想像有一天能在現實世界中與對方相遇,「他們也相信,虛擬實境有一天將變得如此令人身歷其境,使更多關係能在網路世界中開花結果。」
許多 VR 用戶已經表示他們體驗到了「幻象觸覺」,親身感受到自己 VR 化身身上正在發生的事。有人說,當他們的手臂在 VR 中被觸摸時,他們的手臂也會有感覺。這種現象在 ERP 中尤其明顯,同時可以加深由純情的肢體接觸所產生的感情。布魯回憶起在他們開始約會之前的那一刻,當時他和卡拉皮蒂安正在互相拍拍對方的頭,這是VR世界流行的 打招呼方式。「我坐在那裡,她輕撫著我的臉,我心想,這也太親密了。」
而非 VR 用戶似乎傾向忽略 VR,他們選擇牢牢紮根於現實世界,並享受面對面約會限定的所有奇妙感受:複雜的約會行程安排、上唇的汗珠,和因為沒發現演唱會只有站席就穿了新鞋去聽導致磨腳起水泡。有些人認為 VR 形塑了一種鴕鳥心態,讓人逃避身而為人在世界上尋覓愛情的過程中時常經歷的不快。
HBO 的新作《我們在 VR 中相遇》(We Met in Virtual Reality)是一部關於 VR 約會的紀錄片。當預告片於 7 月在 Twitter 上發布時,布魯回憶起他在網路上看到很多惡意中傷的批評。有人留言「這真難堪」或「他們為什麼不到現實世界就好?」。
但對很多 VR 用戶來說,享受線上約會並不是為了避開更遼闊的現實世界,而是接近它的一種方式。
「我們的許多用戶住在小城鎮。」馬倫說。「有些人因為從軍而奔波各地;有些人在現實世界的社交場合中有社交焦慮;有些人受限於需要輔助的生活型態。人們有時可以在這些虛擬形式中感受到最好的自己。」
擺脫現實的庇護所
VR 也可以成為用戶安全地試驗自己的性向認同或性別表現的空間。根據 Flirtual 的聯合創始人安東尼・譚(Anthony Tan)的說法,Flirtual大多數用戶年齡介於18至30歲,其中50%的用戶認為自己屬於 LGBTQ+族群。
卡拉皮蒂安說她在性別轉換之前,有時會進入一個私人的 VR 世界,並切換到女性化身一段時間。她也在 VRChat 遇到了很多跨性別朋友,他們給了她足夠的安全感,讓她能繼續轉換自己的性別。
「在使用 VR 之前,我所處的環境不太接納我。」她說。「VR 給了我一群夥伴,讓我勇於探索。」

回到外太空,我和 CC 玩了山寨版的「節奏光劍」(Beat Saber),這是一款熱門 VR 遊戲,讓你用光劍在不同歌曲的節奏中砍擊彩色方塊。這很好玩,我只有不小心砸到咖啡桌一次。CC 迷人又健談,還熱情地幫助我理解複雜的 VR 世界。CC 在我們的第一次虛擬約會如實赴約,不像我在 Nevermet 上遇到的第一個人,在約定時間後的一個小時才傳訊息給我說抱歉忘了時間。不論是在 VR 或是現實生活,那是我第一次被放鳥,雖然很討厭,但我慶幸自己那天不需要為了約會而離開沙發。
不可否認地,我與 CC 的星際相聚並不是真正的約會。當我們第一次配對成功時,我向 CC 解釋自己是一名記者,正在寫相關的報導,CC 自告奮勇地同意帶我到處看看。無論如何,這可能是最好的狀況。CC 告訴我,他最近開始在 VR 中跟某人約會,對象是他在 Nevermet 上第一個配對成功的人。他們沒有「超級正式」的在一起,但「關係」進展順利。兩人在現實生活中的車程距離只有一個半小時左右,但當我問 CC 他們有沒有計劃要見面時,CC 猶豫不決。「部分原因是疫情讓我對健康感到擔憂。」CC 說。
CC 注意到疫情期間的 VR 用戶數量大幅增加。對於那些待在家裡、有錢有閒的人來說,VR 似乎是一項有吸引力的科技工具、一種擺脫現實世界的平庸和恐怖的簡單方法,並在不冒著吸入有害病毒之風險的情況下,與他人交流。如果還能結識新朋友、與他們談情說愛,甚至來場異國情調的約會?再好不過了。
不過,很難說這場疫情是否開啟了虛擬實境的新時代。儘管 Meta 和 Google 等公司都在大力支持 VR,但它幾十年來的發展一直遲滯不前,從未真正起飛。
1989年,《紐約時報》的頭版報導中描述了這項技術:「戴上特殊的頭盔和手套,人們會感覺自己沉浸在電腦生成的三度空間中,並能以自然的手勢來控制電腦。」記者安德魯・波拉克(Andrew Pollack)寫道:「有朝一日,兩個人可能會在不離開客廳的情況下一起打虛擬網球。」
三十多年後,頭戴式耳機看起來與當時的頭盔仍無太大區別,雖然價格要便宜得多。1989年,VR 頭盔和手套的售價可能高達20萬美元(約635萬元新台幣)。時至今日,Meta 的一款 Oculus Quest 2 耳機售價為399美元(約1萬2,670元新台幣,比8月1日之前的售價299美元〔約9,500元新台幣〕更高)。
儘管 VR 愈來愈受歡迎,它仍相當小眾。 Flirtual 的聯合創始人譚估計,世界上只有大約2,500萬台 VR 頭戴設備。相較之下,任天堂僅在2020年4月至9月,就售出了超過 1,200 萬台 Switch 遊戲機。
現階段,VR 的用戶增長多來自於父母為生日、聖誕節,或純粹為了分散注意力而買給孩子使用,但譚希望 VR 能夠傳播到 Z 世代和現在的核心使用玩家以外的群眾。
「就連我的父母或跟他們同個年齡層的人,只要體驗過 VR 後也會滿喜歡的,所以我認為他們會試一試。」譚說。不過,在 VR 普及前,他認為 VR 約會的成功與否將取決於口耳相傳,就像 Tinder 和 Bumble 在網路約會被去污名化之後,變得更主流一樣。
「我們建立了真正的關係,我認為這足以證明它對人們有效。」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