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森林在自然屬性上對火災很陌生,可是森林確實在燃燒著,僅僅在歐洲,每年就有幾千平方公里的林地遭此劫難
森林是一座大型的能量倉庫——在這裡不論是活著或死去的生物量,都含有數量驚人的碳。依森林的類型而定,每平方公里林地上所蘊藏的碳,可高達十萬噸以上,相當於 36 萬 7,000 噸的二氧化碳(重量增加是因為碳燃燒時會結合兩個氧原子)。此外,針葉林裡的樹還包含了危險易燃物質:樹脂以及其他易燃的碳氫化合物。也難怪總是不斷有森林會起火燃燒,並引發一燒就經常是數月之久的火海。大自然在這裡出了什麼差錯嗎?為什麼演化會帶來這種等同於無蓋汽油桶的產物?
畢竟闊葉樹就向我們示範了情況也能有所不同,它在活著的狀態下,對火是絕對免疫的,這點你自己可以輕易地測試出來(不過請只在一根綠枝條上實驗)。事實是:不管用打火機點多久,這根枝條都不會燒起來。雲杉、松樹及其他同類的樹則截然不同,即使在活著的狀態也都是易燃的。為什麼呢?

在森林生態學家之間流行著一種說法:在緯度較高的北方,也就是大部分針葉樹的故鄉,火災是一種自然的更新過程,甚至有益於物種多樣性。舉著「林火創造物種多樣性」的大旗,在德國的國家林業行政暨學術研究機構的聯合入口網站(waldwissen.net)上還刊登了一篇歌頌林火的文章。
基於好幾個理由,我認為這種主張實在有點詭異,而其中之一就是「物種多樣性」這個用詞。因為,如果真要針對這個主題進行計量式論述,至少得先知道我們的森林裡到底有多少物種;然而,即使在相對算是研究得比較深入的中歐地區,至今都還有許多生物尚未被發現。就連已經發現的物種,也常因棲息環境沒有被充分研究,根本也沒人知道牠/它會出現在何處。而所謂的「發現」,充其量不過代表著牠/它曾在某地被目擊、並加以描述。
一種在我宿舍後方那片森林裡被研究者發現的小型甲蟲,只在萊茵–法爾茲邦境內的另外兩個地方被看到過,而且時間還得回溯到 1950 年代。所以這算是極罕見的物種嗎?我們無從得知,因為就跟許多學科領域一樣,沒有經費就無法進一步研究調查。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出現在我家後面森林裡的這種象鼻蟲,必須仰賴長期不變的環境條件才能生存。而且因為老林地裡的這些條件歷經數百年,或甚至是幾千年都很少有重大變動,所以這些小傢伙喪失了飛行能力。畢竟樂園就近在咫尺,牠們又何必浪跡天涯?
因此,這種昆蟲族群在漫長的歲月裡,始終如一地定居一處,也就完全不足為奇。牠們的出現於是也被視為一種指標,表示此處的森林,處於長久相對未受干擾的自然狀態。而一場森林火災,將導致這個系統完全失衡,而且它所波及的面積還可能相當廣大。那些體型迷你的森林住民該往哪裡逃,尤其是:能逃多快?以象鼻蟲走路的速度,勢必逃不過猛烈火苗的追擊,而牠們又早已無法飛行。沒錯,對我而言,這一切都指出了一個事實:大多數森林在自然屬性上對火災很陌生。
不過,森林火災在本質上卻到處被視為自然現象,而讓我覺得這件事很怪異的,還有其他的原因:人類自好幾十萬年以來就懂得用火,根據對「人」的定義不同,這時間甚至還可以往前推得更長遠。例如:若把我們遠古的祖先——如直立人(Homo erectus)——也算進去,火早在一百萬年前左右,就已經出現在我們先人的生活中。這點是由在南非進行研究的學者所證實,他們在一個名為奇蹟洞(Wonderwerk-Höhle)的岩洞,發現了當時人類以樹枝及草升火烹煮的明顯痕跡。另外,對直立人牙齒的檢驗分析,從而讓人推測出以下結論:人類開始用火的歷史,甚至有可能是原先所認定的兩倍長;而且因為開始喜歡熱食,現代人才能發展出容量如此之大的腦。因為熟食不僅熱量較豐富,也較容易咀嚼且較好消化,難怪從此之後,火與人類不可分離。
因此火災早就不必然是種自然現象,它在我們祖先初露曙光的文明中,是任何生活場域都會出現的首要效應。那我們該如何區分一場火的成因究竟是自然,還是人為?就我的理解,只要一地同時存在著人類與樹木,從那時候起就再也分不清了。我們今天怎麼有辦法,從充滿焦炭的堆積層裡,確認出森林大火的起因是一道閃電,或者是一名用火的穴居人?所以過去經常出現林火,且森林也因此不斷更新,當然就絕不能解釋為是自然的規律,那頂多是種會伴隨人類聚落出現的現象。
能夠駁斥火災是森林自然現象的有力論點,還有那些個別超高齡老樹的存在。譬如說,挺立在瑞典達拉那省的雲杉「Old Tjikko」。這棵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樹,經科學家分析後,確認已高齡九千五百五十歲,而且還能繼續活得更老。假若在它一生中,曾有林火肆虐過這個區域,那麼 Old Tjikko 肯定早已駕鶴西歸,無法活到今天。
可是森林確實在燃燒著,僅僅在歐洲,每年就有幾千平方公里的林地遭此劫難,尤其是南歐地區。其原因很多,首先是許多森林遭到砍伐,而早在古羅馬人大興海上艦隊時,就已經對這整個過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許多林地之後變成矮樹灌木叢生,再加上接下來有大批的牛、羊被放養在此,因此幾乎沒有任何一棵樹有機會長大,於是此處的林相再也無法恢復。這樣的灌木草原,無論是在過去或是今天,都毫無防護地暴露在炙人的豔陽下,為火燄奉上它乾燥的灌木叢及草堆,來作為最佳燃料。其餘通常由不同櫟屬樹木組成的森林,近來則多半由松樹與尤加利樹栽培林所取代。與橡樹這類櫟屬樹木相反,要讓這兩種樹燃燒起來簡直是輕而易舉,這點清清楚楚反映在過去幾十年的森林火災統計上。
不過要燃起火苗,到底得先有那源自某處的星星之火。而那只有在極罕見的情況下才會出自閃電,沒錯,真正讓森林燒起來的原因,是因南轅北轍的動機而心懷鬼胎的人類。它經常牽涉到建地,而依照規定這在森林裡是不被允許的;可是如果森林「消失」了,新的飯店與住宅當然也就有機會出現,就像 2007 年那幾場毀滅性大火之後的狀況,僅僅在希臘就燒掉了超過 1,500 平方公里的森林,其中也包括了凱爾法湖(Kaiafa-See)保護區裡的 7.5 平方公里。然而,事後希臘政府的處置方式,不是讓這些區域繼續回歸自然,而是讓觀光業者在那裡大興土木,並讓原有的八百棟左右的非法建築就地合法。更糟的是某些心懷叵測的消防人員:為了不丟掉工作,有人居然會乾脆在風平浪靜的太平時期自己製造火警。
因此多數火災有個共同點:都可直接或間接地歸咎於人類的行為。肇始於自然因素的火海煉獄基本上沒有,然而如此認定,卻能為林業經營者採行的皆伐提供絕佳的藉口:因為如果這是一種自然現象,那採伐時把一面積內的樹木全部同時砍掉,應該也就不會有什麼大礙——畢竟大自然很習慣地表出現這樣的空白。
但是情況正好相反。歐洲的闊葉林尤其具有「歷久不變」的特徵,因此這些樹並沒有發展出防火對策;它們雖然在活著的狀態很難被火點燃,樹皮卻無法耐受高溫。像山毛櫸樹對此就非常敏感,當它位在林間空地邊緣時,甚至還會被曬傷。
即使林火在全世界絕大部分的森林都是罕見的例外,還是有些生態系統適應了這類事件。不過它們所適應的,不是那種讓所有樹木都付之一炬的巨燄——不管在地球的何處,這對森林來說都是意料之外的大災難——而是在地面延燒的火。這種林火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為它所摧毀的只是底層植被,如草本植物及雜草,而不是樹木,或者至少不是那些老樹。從老樹的樹皮就足以得知,它們天生具有暫時耐受高溫的裝備。
名列世界最高大樹種之一的海岸紅杉(Küstenmammutbaum)正是如此。它能長到超過一百公尺高,還能有幾千歲那麼老,且樹皮又軟又厚,還具有阻燃性。如果有幸在某個城市的公園裡看見這樣的樹(世界上還真的有許多城市的公園有它的踪影),不妨走上前去,用拇指按一按它的樹皮——你一定會訝異於那有多柔軟,而那是因為裡面鎖住了比例很高且能完美隔絕高溫的空氣。因此,紅杉的樹幹能夠在火線快速通過時毫髮無傷,而這正是一場夏季的草地或灌木野火會帶來的狀況。
不過這種方法只保護得了較老的個體,年輕的紅杉因為樹皮還很薄,就時常會在大火中嚴重受創,甚至完全燒毀。因此這些紅杉巨木在它們漫長的生命中得顧慮著林火,但是它們並不需要林火來活下去——這兩件事經常被混為一談。而且,它們也順帶表明了一點,那就是即使是適應了野火的樹種,也不想被大火燒死,事實正好相反:只要一地的生態系統先天就免除不掉林火這要素,那裡的樹木就會讓自己配有極不易燃的裝備,這樣一來,整個區域也才不至於化為灰燼與焦土。
同樣以北美西部為家的美國西部黃松(Ponderosa-Kiefer),也讓自己披上一身厚實的樹皮,以保護那極為敏感的形成層,即樹皮與木質組織之間的生長層不受高溫傷害。然而,與紅杉巨木一樣,這招也只在頗有年歲的樹幹身上,以及當火燄不及樹冠高度時才會有效。樹冠上有著充滿易燃物質的針葉,只要這裡著火了,火苗就會從一棵樹跳躍到下一棵,並摧毀整座森林。這些總被認為是自然野火代言者的樹,其實只表現出以下的事實:它們連自己都痛恨這個自然元素,並且也只因自己潛在的長壽,才能從罕見的雷擊及其所引發的地表火中找到應變之道,而這種適應成功又讓它們活得更老。
那備受讚揚的「透過火燄把營養物質釋放出來」,一種林火能夠循環回收死去生物量的說法,在我看來不過是神話,目的是要緩和人類自遠古以來,就不斷以火干擾這個敏感的生態系統的事實。因為撬開大自然所儲藏的養分,並使其成為新植物生長所需之腐植殘餘者,通常並不是火。沒錯,完成這項「骯髒」任務的,是數以幾十億計的動物性清道夫大軍(而在一場森林大火中,牠們的命運是被燒個精光——可惜這些「討厭鬼」的皮不夠厚)。
本篇文章轉載自《自然的奇妙網路》一書,原文標題為〈熱到最高點〉, 2018 年 12 月由商周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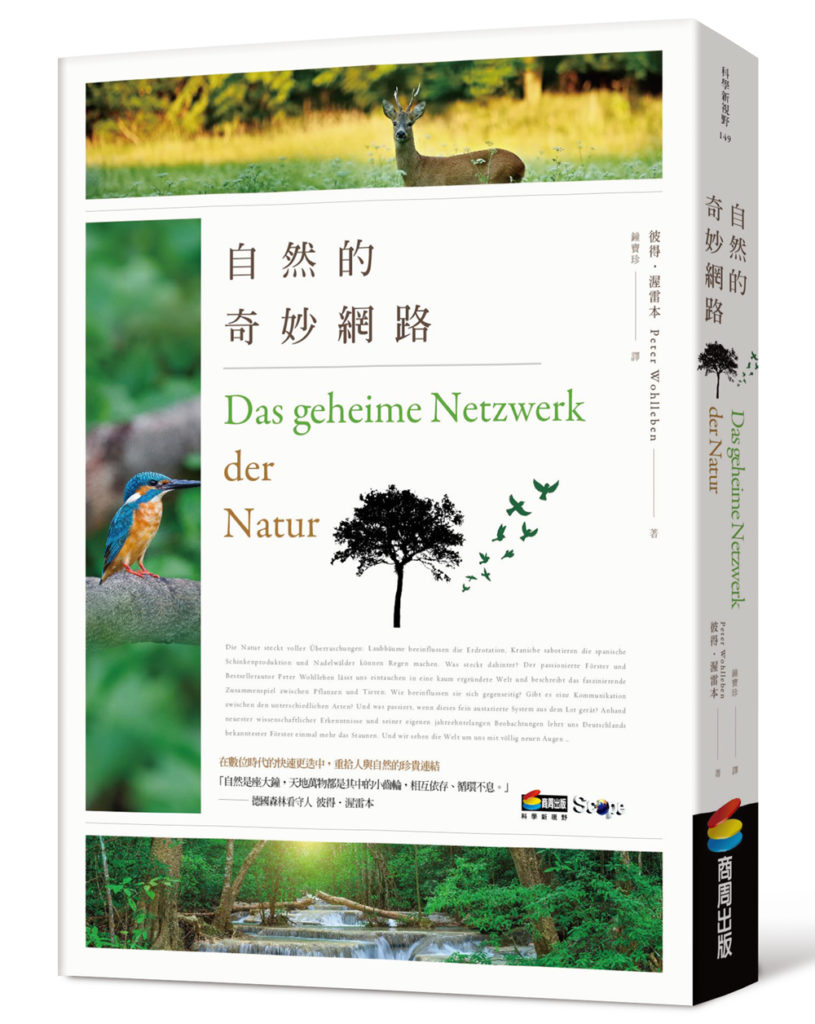
商周出版
NTD $360 平裝 / 3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