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礫、浪花、鬼、魂與路上的個性——讀旅行文學的孤峰之作《故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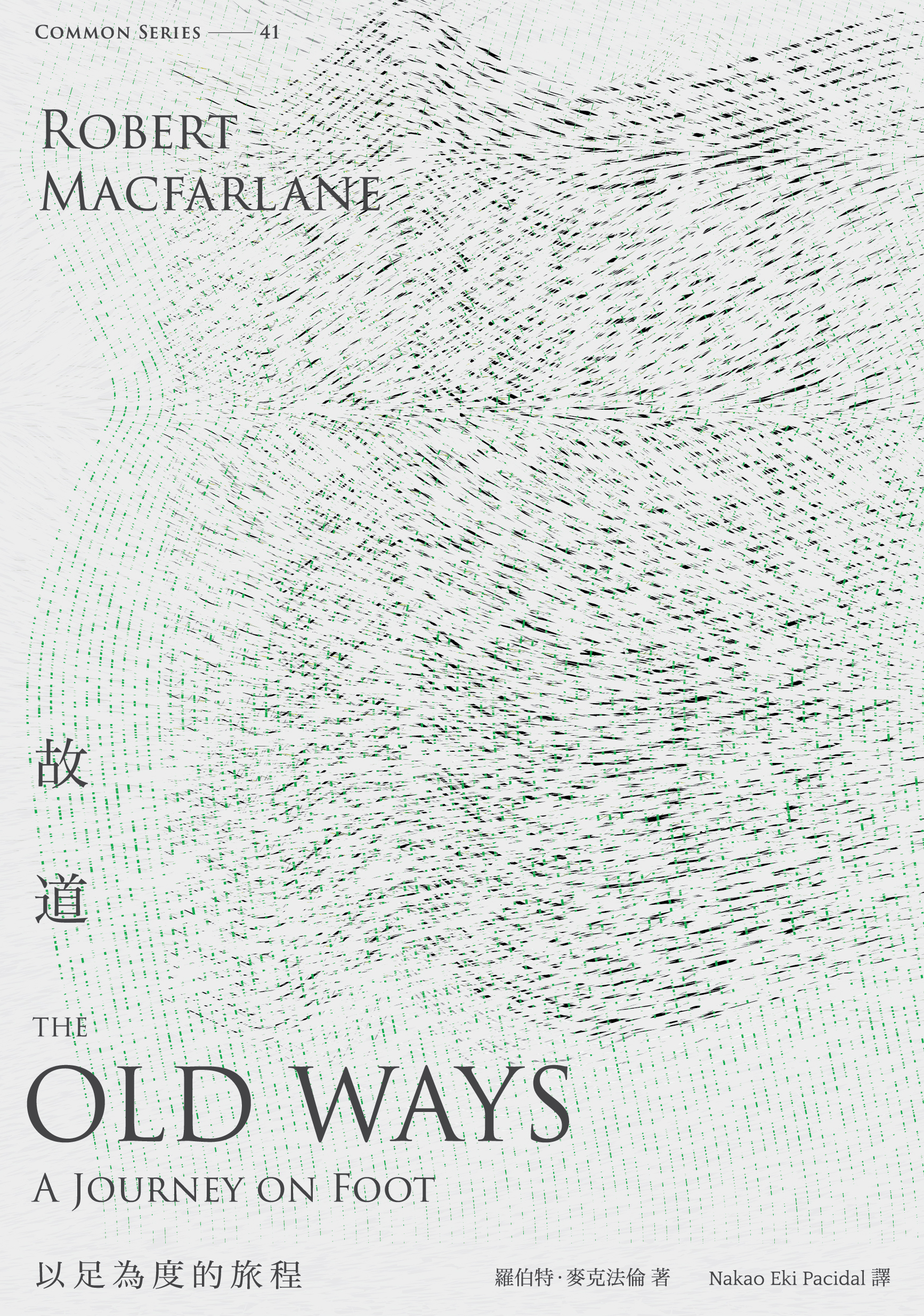
羅伯特.麥克法倫
大家出版,NTD $420,平裝 / 448頁
山之心
有好一段時間了,我一直想著我們應該對深刻的地景提出兩個問題:首先,當身處此地時,我認識了什麼,而這又是我在其他地方無從知道的?其次再徒勞地問:此地知道多少我所不自知的自己?
《故道》,43頁
個人的閱讀必定充滿偏見,這一次,我的偏見是:英格蘭青壯作家羅伯特.麥克法倫的《故道》,是我讀過的旅行文學著作中,幾近沒有匹敵者的孤峰之作。稍稍回想一下,上一回能有這麼巨大快感的閱讀經驗,要算是馬奎斯的《百年孤寂》,而那已是遙遠的往事了。
《百年孤寂》是小說,《故道》是非虛構類散文,但它們都織繪了壯闊深沈的「生命地理學」場景,我揣測,也許是那種延伸到海角天荒的空間尺度,交錯著上升與沉淪皆深邈的人心探查,敘事結構錯迭相扣(也可說是一種恰如其分的緊繃),卻又表達於白描、內省且安靜的文字句組中,所以《故道》中好幾道的思維束線得以躡手躡腳、漫漶穿透進現下台灣百無聊賴的無意義生活世界,於我產生這麼大的撞擊力,雖然作者不過只是邁開雙腳,走上一條條少有人跡的遠古步徑,向著隱隱召喚他的一縷先人幽魂,探問啟蒙的蛛絲馬跡,而已。
讀完《故道》,台北封閉的城市景觀突然門戶大開,感覺到孤涼山徑的草葉於遠方竊竊私語起來,原來,刻板和重複的生活仍有重大可能,生命終是朗朗自由——只要靈魂能夠抖擻起來,起身上路。我想,近年來許多被戶外情懷所莫名吸引的同好們,應都或有類似的同感吧:一旦「自然地景掙脫了風景畫框(landscape scapes),它便活力飽滿而且勇於製造騷動,透過每一個時刻、每一樁事件,形塑著走路人一生的生命敘事。」
不僅是這本《故道》,麥克法倫「地景與人心三部曲」的前兩本書——Mountains of the Mind 與 Wild Places,也都從人類情感與自然交會的系譜學研究開始。必定是得力於網際網路的查找便利,以及遙遠訪問聯繫電郵往返之簡易,或可再加上英國浪漫主義數百年來的心靈遺緒,一九七六年出生的麥克法倫,展現了前輩作家難以企及——文獻縱深如此悠遠、地理規模這般弘大;人物行徑百般殊異,但心意卻又極其深邃——的人類心靈活動圖譜。
不論是山岳、荒野或古道,在我輩有限的歷史視界之外,早已有各種踽踽獨行於其上的先鋒探查者,許多更或可早於書寫文明誕生之前,因而,揣度或極盡合理地去探尋他們的蹤跡,去理解歷史人物那一刻的當下思緒,於寫於讀,便具備著一種系譜的魅惑,那些曾洶湧過某些人心的山、荒野和古道如今都依然在那(雖然後者愈來愈得費勁才得尋獲),人人皆可親臨現場,一方面,系譜敘事引領讀者逆溯回昔日的背景下閱讀,另一方面,讀者也必定把它放入今日的場景中感受,這是現代人追求獨特生命經驗的新興閱讀需求,而麥克法倫絕對是這套技藝中最出類拔萃的行家。
系譜學原來的旨趣,是探討家族血緣的源流圖譜,是對於起源的探索,也在於釐清脈絡,以滿足財產繼承的鑑定需求。但在十九世紀哲學家尼采那兒,系譜學卻成為一種解構的技藝,考察觀念和物件在歷史中如何被逐步安排與設定,他的《論道德的系譜》指出,基督教社會中的「道德」有多種意義:它既是結果、癥候、面具、偽善、疾病和誤解;它也是原因、醫藥、興奮劑、抑制丸與毒藥。麥克法倫的系譜學當然與尼采的用意不同,相較「道德」在人類社會的源遠流長,「自然」仍是一種青澀與懵懂的情懷,雖然,就某種意義來說,這種返歸「自然」的情懷,正孕育著尼采解構「道德」後所標舉之「超人」的自我育成之路,是當今最具時代感的議題之一。
《故道》的系譜研究這般地引人入勝,一部分原因,在於古道那湮沒著卻永不消失的特質,歷史中數百個世代將它踩踏成一條隱密卻可踏查的步徑,有限生命長度的人們透過代代接力,於此頑抗著自然,步道因此藏有特別的時空張力(墳塚、疊石、洞穴、歌謠⋯⋯),引人好奇追索;另一部分原因,是時光中各個不同的行路人,懷抱著個別時代感的意義情結踏上古道,知曉這些故事,有助於我們這些「去歷史感」的工商社會人定錨自身,例如,麥克法倫親自走上的那條東英格蘭掃帚道,全憑著一雙腳捉摸水波下硬挺的砂石,方能辨識茫然海平面上那絲縷一測的走行方向,於此,脫下鞋襪的讀者便接續上那個科技仍未萌芽,但人們身體感官仍主掌知覺和判斷的古典時代,分享了一樣的躊躇忐忑與三分身心蕩漾。
身為旅行作家,「地景與人心三部曲」自是麥克法倫身歷其境的作品,三部曲壓艙作《故道》尤其如此。從劍橋大學住家旁邊的伊克尼爾古道開始,往西北來到白浪滔滔的大西洋外赫布里底群島,往東去到以色列控管的巴勒斯坦屯墾區,再向東來到圖博高原貢嘎雪山的轉山之路,作者背著帳篷與睡袋,進入風霜雨雪,折斷過幾根肋骨,迷失於古道也數度新生於古道。
這中間最關鍵的環節,是麥克法倫開放地敞開身體的感官,讓當下的經驗如電流或水流般灌滿全身(當他學會操槳時,他感到大海這名「藍人」將力量輸送到了他的臂膀,而那只瘦骨嶙峋的舵柄,則成了他胳膊的延伸。走在路上,腳自然會思想,因為走過的地方,花崗岩會「閃閃發亮,紅紅的,如新生成的石頭」),據此,作者與遙遠的前行者對話,也與那事事想當然耳的純理性之我,對話著。這些對話,有可能是對前人之語的加以確證,也可能是更深刻化了那些系譜中的敘事,也有可能當下這些身體的感受仍無法解開歷史謎語,只得把問號埋藏在腳底板或忘不掉的嗅覺中,當然,也有可能自身的衝擊或冥想是全然新鮮生動,不與他者對話便足以滋潤生命,如貢嘎雪山腳下那轉完山、一身泥濘的從容喇嘛那樣。
然而,我們當然也都知曉,不是所有現代作家都能擁有這等身體的技藝,而通常,身體技藝的敏感和嫻熟與否,也幽微地左右著作品的原創和特殊與否,這道理其實不難理解:每個人的身體其實是認識世界最本真(authentic)的起點,同樣的一片陽光自然會有萬千種情懷,反而是那些讓人們得以彼此溝通的語言的內在結構,在嬰兒開始接受教育後,倒過來模塑人們成為零差異的大眾化群體——能複製但無法創作,擁庸見卻不覺其腐。在閱讀過馬奎斯的傳記或者麥克法倫「地景與人心三部曲」之後,我們應當都能肯認一件事:愈是刻骨銘心的經驗,愈是能構成獨特的敘事,並且以其真誠與反思,調動起強大的說服力。
《故道》的另一個顯明啟示,便是提點著現代讀者,如何讓自己的身體具備一種抒情的技藝之同時,而又能自歷史和田野觀察中,獲取一種節制的知性。
要讓自然能走入內心世界,當然是先要讓作為情報接收端的身體,具備捕捉事物細節變化的敏銳能力,有「美國國家公園之父」之稱的約翰.繆爾這麼說:每當他出門走向山,山便走入他心中,行路愈長,滄桑多了,身體知曉萬物的本事便愈來愈有靈性,然而麥克法倫也提醒著,驅使人們上路的動機,往往並非是那身體純然求知的渴望和衝動,而更毋寧是生命和心理上糾結的陰影謎團,它們源自主人翁的童年或前意識的更早,糾纏一世。行路人是藉著身體於地景中的遭遇式感動,對抗著也理解著自身這巨大的抑鬱和疼痛。麥克法倫很直白地承認,整本《故道》的起心動念,便是對二十世紀初英格蘭年輕詩人愛德華.托馬斯其意外的才華和意外的命運的追索,這本書的第十四章〈燧石〉說了這故事的始末,是任何人讀了都很難不泫然淚泣的一章。
「我途程中的路標不是只有支石墓、古墓和長墳,也有去年的岑樹葉(手心一捏就碎了)、昨夜的狐狸糞(仍充斥鼻端),此刻的鳥鳴(尖銳刺耳),高壓電塔那詩意的滋滋聲,以及農田作物灑水器的嘶嘶聲」,這些記憶中的細節,來自作者多種身體感覺的輔助,即便異地時空,讀來依然栩栩如生,但細心的讀者也絕不會忽略他引述卡繆所言:「他於是能寫一個當代人的故事,他的心碎唯有長時間地對著地景沉思,方能治癒。」
公元五世紀左右,一種對修士的身體實踐極為嚴苛,且植基於一種獨處理想意念的虔敬儀式,從今日法國的高盧經由海路,傳到了不列顛島的西部和北部,這種生活風格於拉丁文中稱作「desertum」(荒野或孤獨之意),而這種風格培育出的信徒叫作「perigrini」(雲遊四方的基督徒),一群 perigrini 張起一面自己的帆,便開始去尋找自己的 desertum,這群人在《故道》裡被麥克法倫隱約看作是「現代人」的先鋒,他引據歷史學家肯尼斯.懷特的描述:(這些僧侶)突然開始離家遠行,在偉大的遷徙中飛翔,腦中裝滿文法學和地理學、動詞時態和暴風雨、敏快的思想和詩歌。在人類文明的漫長時空中,這一少數的先行者,是最早揚棄永恆與安定的意念,於大自然對人的磨難中提取個人化人生滋味的人,他們於變動中不以為苦,明白日新又新的體驗(即便有時須付出生命以為代價)使生命無所虛度,且對來日溢滿探求的渴望。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在他的文化社會學經典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勾勒的也約略就是這群基督教世界的叛逆後裔,如何在對死後永生的宗教追尋裡,意外地卻也合理地,孕育出對個人生命意義的確證感和主導欲。如果透過尼采的比喻來說,起初是人們依照自己的理想形象創造了上帝,讓眾人得以依循,而當人類發覺自己的理想浮凸在遠界與他鄉,並對其興動了追求的英雄念頭之後,上帝隱沒的時刻也就到來了。
這也是閱讀《故道》這本詩意的雄心壯志之書,對台灣社會別具時代意義之處——當舉國上下都在尋找破壞式創新的那個破口或轉折之際,它考察現代性的內在系譜後娓娓道來:是個人創造了時代,而不是時代創造了個人,當每一個時代壓制了個人,人們便找上一條人煙稀少的路,拓荒而去;路徑並不通向任何答案,路徑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