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尼采一起登山(或下山):成為更真實的你!
Access to Too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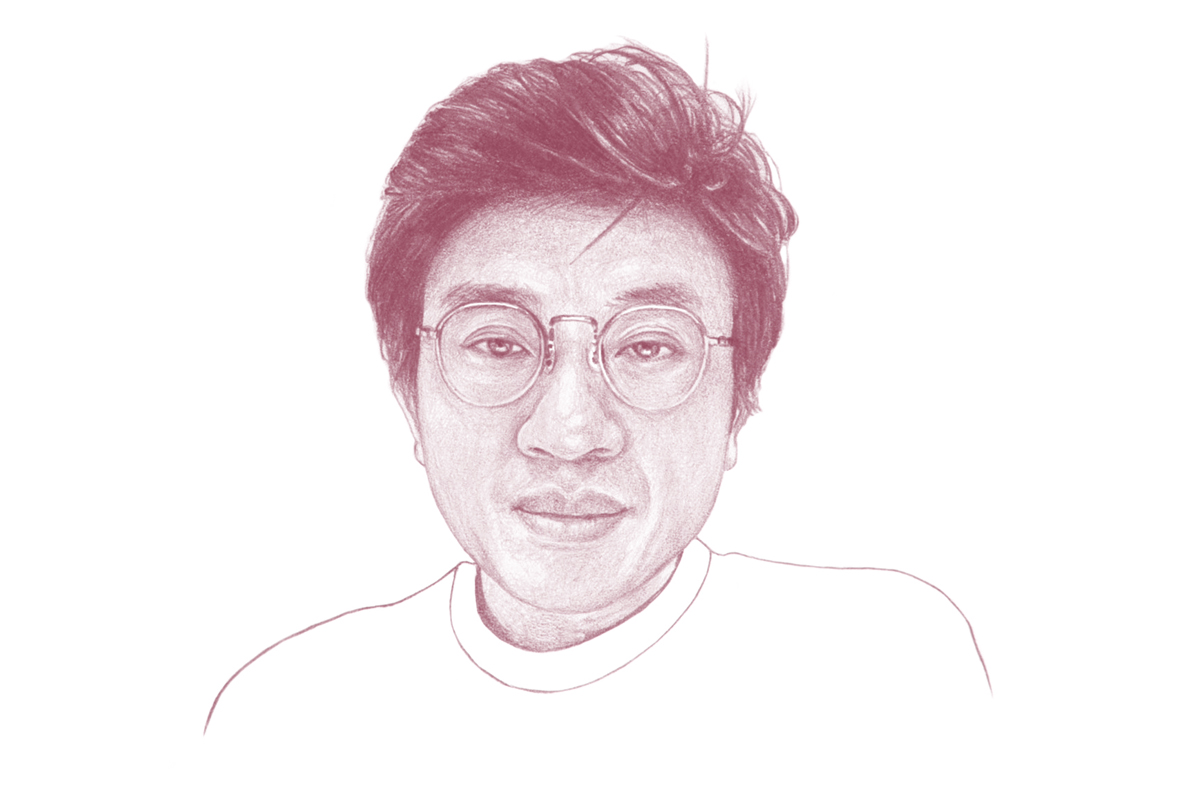
登山背包與裝備已經打包完成,雖然外面下著大雨,明天一早6點前就會出發前往奇萊,明晚此時如果沒有被大雨打敗,我打算後天上攻奇萊主峰,前進奇萊基地營的成功山屋紮營過夜,希望照計畫登高攀頂,走過主北峰之間傳說中壯闊的高山草原,預計週日傍晚回到地面。
這個時候挺適合介紹一本我最近正在讀的書,約翰・卡格(John Kagg)的新書《跟尼采一起登山:成為真實的你》(Hiking with Nietzsche: On Becoming Who You Are,暫譯)。
尼采跟現代哲學/社會學的發展有著密切卻常被忽略的關係,傅科、奇美爾、阿多諾、海德格、拉圖⋯⋯許多我心儀的學者都受到他的影響,但要跨過刻板印象、準確理解尼采並不容易,卡格發現一個理解其思想最恰當的方式,起身跟著尼采的腳步走入瑞士與義大利邊界的阿爾卑斯山區,在一步步趨近山的路途上體會尼采的肉身掙扎與精神蛻變。
驕傲的獅子
事實上,這正是卡格本人做過的事,而且還是兩次,19歲那年他的哲學老師給了他一個裝了3,000美元的信封,要這個方正規矩的大男孩走出封閉的斗室、停止苦思冥想的內心辯證,「去!去瑞士,去走一趟尼采走過的路!」然後他在37歲那年成家有了小孩之際,碰到不耐重複單調生活的中年危機,決定帶著一家三口重登尼采與年輕的他走過之舊路,《跟尼采一起登山》正是紀錄了這趟療癒的哲學反思旅程。
尼采出版了《悲劇的誕生》後成為一位學院的異端,他糾纏人事困境之後決定放棄「努力融入學院」的日常、主動選擇離開大學所在的巴塞爾前進瑞士小鎮施普呂根,從那裡走入阿爾卑斯山,踏上與孤獨對話的歧路;從毀棄安定秩序、面對未知中鍛鍊「成為真實自己」。卡格這本書讓人讀來欲罷不能,交織著尼采的行思與作者的人生體會,青年中年的尼采與卡格不斷地在山屋斗室、在冰原懸壁、沿著崎嶇山路對話辯證,一個精采等身大的尼采於焉誕生,跟我這位台灣的中年山友,一位青春遠去、年輕時的衝撞血氣不再,一面仍夢想著再做一件「或許還有可能」的事,一面天天陷在中年老爹育兒瑣事的社會學家交心。
卡格的前一本書是《美國哲學:一則愛情故事》(American Philosophy: a Love Story,暫譯),聽到「美國哲學」就知道他跟我一樣,是對艾默生(Ralph Emerson)與梭羅(Henry Thoreau)的「超驗主義者」(Transcendentalism)素有好感,又敬仰詹姆士(William James)與杜威(John Dewey)的「實用主義者」(Pragmatist)。這個契合讓這趟跟著尼采一起的「登山閱讀」充滿了與好友重逢的喜悅,三位中年男子一起回首來時足跡,低頭檢視當下、體會中年的喘息,朝那不可企及的高聳山巔望去,暢快結識會心交流。
契合的地方不只於此,還有從卡格的山友尼采口中得知,跟我長期關心的「民藝」恆久緊張的內在關係:「永劫輪迴」(eternal return) 如果是「成為自己」的障礙,不就否定了在不斷重複的日常中出現「美學自我」(aesthetic self)的任何可能?中年男子脫離學術體制的奮力一搏會不會只是薛西弗斯的徒勞悲劇?如果最終證明「失敗」,那會是怎樣意義的失敗?如果「成功」,會不會反而象徵了最終的墮落屈服?還是,男人一生最後的一場花火,迎的只是終於超越了「成功/失敗」的那一瞬美感?尼采應該會回答:「只有勇於離開平地、向山靠近的人才知道。」
那不能殺死我的,使我更堅強。
「大多數的男人,那些獸群,從來沒有嚐過獨處。他們離開了父親與母親,但只是接著爬向太太,默默地屈服於新的溫暖與新的關係。他們從未落單,從未跟自己傾訴。」
所以,我該停筆,準備明天與奇萊(已經經歷三次失敗撤退後)的第四次約會!
純真的嬰兒
登頂奇萊前,路上白霧瀰漫的碎石坡很陡、由谷底捲上的風很強,連大人都不易站穩,冷冽空氣讓戴著濕透手套攀爬上山的我們陷入兩難,是的,我帶著家裡唯一的小男孩 Kaya 一起上山,那一刻我們非常疲累已走了10小時,腳下就是身體必須懸空「暴露感」十足的懸壁。作為父親,我也只能在距離之外「見守」,看孩子聚集自己全身的力量,學著在每一步的當下料理自己,學著細膩冷靜地處理沒有人可以替代的狀況,孩子必須克服恐懼與困難,一個人前行。
第二天傍晚,我們拖著一身疲憊與滿身塵土的裝備,在高鐵台中站的速食店裡等著北上返家的列車,山剛給孩子上完一堂珍貴且能受用一輩子的課,Kaya 很勇敢、很專注,父親眼中的「辛巴」學會了獨立,累積了自信,驕傲的老獅子很高興陪孩子走過幽谷登上山峰。
我們在奇萊山頂收到一個意外的任務,為應援台灣登山家張元植與呂忠翰攀登世界8,000公尺高山的 K2 Project 拍攝一段「島嶼天光」的大合唱,孩子似懂非懂跟著唱了。我在速食店裡拿手機給他看了 K2 的資料影片,突然好奇小男孩究竟怎麼看待這件事。我碰過的朋友遇到 Kaya 本人,沒有一位直覺相信這麼瘦小的男生會出於自願登高,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裡克服「永劫輪迴」的「精神三變」足以激勵老男人的鬥志,但那跟小男孩的距離恐怕遠超過 K2 的抽象高度。
我們父子一起爬了那麼多次山,從沒好好坐下來聊過「山與登山」,意外地我們在高鐵站速食店的 Men’s Talk ,話匣一開嚇到了我。這孩子的回答不脫稚氣,但童言童語中卻對自己經歷過什麼、有什麼感受,有著超乎我想像的自信,透露出一種毫無矯飾姿態的哲學清明:
J:Kaya,登山有時很痛苦你也知道,但是為何你看那些大哥大姐都很喜歡登山?你可以了解嗎?
K:每次下山後,像現在我在速食店,雖然外表沒什麼改變,但我感覺裡面突然變得比外表更大了,更有力量了。嗯⋯⋯就是好像寶可夢一樣,要開始「進化」!像有一種「新的力量」在身體裡面一直要衝出去,也不知道要跑去哪裡!
J:我懂我懂,那你覺得山為什麼會有這個魅力?
K:嗯⋯⋯(沉思了好幾秒),應該是因為「高度」吧?
J:是耶,山基本上就是高度的現象,還真一定跟高度有關。但為什麼?你愈爬愈高時都在想什麼?
K:嗯,怎麼說,就好像山頂上「有什麼東西」在等著我。
J:(愉快大笑)我好像也懂那種感覺耶,但那是「什麼」在等你?你到山上有沒有遇到?哈哈。
K:嗯⋯⋯我想應該就是「頂點」吧?愈爬愈高,你看東西的「角度」就不一樣,只有在頂點才有那個角度啊!(兩手作勢比給我看)
J:山最高的地方一定是「頂點」,但「角度」?
K:「頂點」可以看得到更多,一定的啊!你在低的地方,先爬到上面的人就往下看你啊!他一定比你早看到什麼!
J:有道理耶!山頂就是那顆山上再沒有比它更高的地方,當然看得最廣!
K:Daddy,不是這樣嗎?只有最高的地方才可以「單純的看」。
J:你是說可以躺下休息不用再爬了嗎?哈哈。然後下山以後呢?
K:你就會開始期待下一座山啊!
J: 但是,爬到山頂前要花好多時間力氣,中間都不好玩嗎?
K:不會啊,因為高度,你就會期待看到不一樣的生物啊。在平地,你看到的都是那些已經知道的東西。但你愈往高處,生物都不一樣了,草啦,鳥啦,樹啦,而且不知道接下來還會碰到什麼。
J:我知道你不喜歡爬郊山,但那也是有高度啊,高山有什麼不一樣?
K:Daddy,低的山都很人工,沒有離開人多的地方,就沒有「冒險」的感覺啊!
J: 「冒險」?什麼意思?你在高山上有碰到什麼「冒險」?
K:不是「冒險」嗎?低的地方人很多,很多規定「一定」要那樣的東西,一定要走,一定要停。高山上凹凸不平都沒有一定的走法,到處都可以搭帳篷,雖然不一定安全。這就是冒險啊,因為到了山上「什麼都不一定」!
J:那你有沒有什麼登山的技巧可以教小朋友的?
K:登山還好吧。你就⋯⋯儘量一小步一小步走,不要走到會喘。還有,山上的石頭,有的看起來很大,但你還是要踩踩試試,繩子也一樣,有的會騙人,石頭會滾下去。啊不就說嗎?山上「什麼都不一定」!
J:嗯,我懂你說的冒險了,那你有什麼登山的心得?
K:沒有啊,就是不要放棄,一直走一直走,最後都一定會走到。
勤奮的駱駝
從奇萊北峰下山之際,我沒有想到那可能是我這輩子最後一次登高山。長年坐姿不良地密集打字與閱讀讓我的健康開始惡化,頸椎受傷的症狀從左手指的一點間歇麻痹,一個月間像飆車般轉變成肩頸背手幾乎無時不止地抽蓄麻痛,連睡眠都要不斷被翻身的痛中斷。
我的其他兩位登山夥伴,尼采在結束一段愛情與友誼糾結、引人非議的三人關係後潦倒落單,偏頭痛、嘔吐、昏眩的舊疾失控,1888年從阿爾卑斯山撤退到義大利溫暖的大城市杜林,在舒適許多的「墮落」(decadence)環境中養病,在不到一年間迴光返照般完成了《偶像的黃昏》、《反基督者》、《華格納事件》等六部最後的著作,耗盡氣力「重估一切的價值」然後再度惡化終至神智不清。
卡格年輕時跟隨尼采的腳步入山,在「超人」(Übermensch) 的理想感召下,經歷了偏執節食的「自我否定/自我控制」差點喪命。尼采終究陷入瘋癲,沒能回到他魂牽夢縈的阿爾卑斯山路,但卡格在多年後帶著妻女,沿途覽讀尼采的所有著作,再度「跟尼采一起登山」,這一次他「成為自己」,學會了接納必然真實而尷尬的中年兩難,下山之際心安理得地回到美國哲學傳統——梭羅《湖濱散記》的超驗主義懷抱。
「驕傲的獅子」跟駱駝象徵的日常集體決裂,脫隊獨自踏上冒險「成為自己」的英雄歧路。但「獅子」並非人類精神演化的終點,連尼采也只能在「超人」之前黯然潰散止步。尼采回顧一生的思想自傳把自己放到耶穌的位置, 模擬羅馬帝國行政長官彼拉多(Pontius Pilatus)向眾人展示身披紫袍,頭戴荊棘,被鞭笞到不成人形的耶穌時的話語,《瞧,這個人》!孤獨的老獅子在病痛纏身、接近瘋狂,進退兩難的困窘中仍堅持「萬獸之王」尊嚴的姿態眼神!
下山之後,我的日子陷入每週反覆進出醫院就診復健的「永劫輪迴」,我戴著口罩枯坐在候診室時經常想起山上的空氣,當然也不時想起同樣思念慕山困在杜林的尼采,想到被他認為「墮落,但也充滿可能性」的山下日常,病痛之前的我不也一直都活在裡面嗎?有一天, 我突然恍然大悟,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非日常」大約出現在三個時刻(moments):節日,尤其是大型的祭典節慶;旅遊,走向高山(或者異國遠行);最後就是病痛,因而入院或甚至住院的診療間。
人生這三道通向「非日常」的門扉,一個把日常的你我「拉高」到宗教的精神高亢;第二個將身體平行「橫移」推離熟悉的都市;最後一道,像今天,把身體「下拉」到靠近病老壞死、陰陰鬱鬱的生命底層。
人的生命有限,卡格、尼采或我都一樣,在「日常/非日常」間眾多虛線間來回穿梭,但「日常」的實相奧義仍舊半遮面貌地跟我們在玩躲貓貓。駱駝重複單調的日常裡藏著希望,或許不該偏執地繼續背向,因為「日常」裡才有所有我們在乎的人事物(everything we care)——孩子純真無邪的笑,事業競技場更有人味的尊嚴,親人噓寒問暖的關切招呼,「我們活著,因我們在乎。我們戰鬥,因我們在乎!」(We live because we care. We fight because we care!)祭典、旅行、登山與病痛,難道不是因為這凡俗世間的尋常「在乎」才有了意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