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與反智 —— 給選民們的書單
由於 2018 十一月縣市長選舉的規模擴及全國,政見又多屬民生議題,綁定大選的公民投票則是直接民主,這次的選舉做為民進黨全面執政之後的中期選舉,指標意味濃厚。而從 2016 年初蔡英文當選總統,兩年之內聲望從高點到大低迷;將眼光放到世界各國,英國脫歐、川普當選、習近平稱帝、世界各國吹起民粹風潮,令人不禁懷疑「民主」是否真能反應時代的變化,帶來正面的解答?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遊戲規則真的能達到所謂的公平嗎?它是否能反映真正的民意呢?或更激進的說,以力求「公平」的方式,求取最趨近真實的「民意」,這個機制真的重要嗎?對國家治理有幫助嗎?真的可以增進人民福祉嗎?

揚-威爾納‧穆勒
時報出版,NTD $320,平裝 / 240頁
《解讀民粹主義》
「民主就在如雷的掌聲中死去」?
台灣人初次聽到「民粹」二字,應該是在解嚴後不久,在野黨礙於國會席次的劣勢,動輒使出非常規的抗議手段,並時時提及「以民意為依歸」,遭到許多當權者與御用學者斥為「民粹主義」,當時台灣仍是民主初段班,許多人只把它當成是保守勢力醜化反對者的手段;然而再一次聽到「民粹主義」,卻是在討論那些老字號民主國家:例如雅典城邦的後人希臘、人權思潮發源地法國、或是號稱世界上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美國,所發生的最新「民意」。不意外地,最喜歡跟風的台灣政壇,又開始使用「民粹」一詞,而且說話的人居然是當年被批評為「民粹」的那些人!
大家對民粹共同的印象就是「反菁英」,而作者第一件要釐清的也就是這一點。誠然,民粹主義者主張自己之所以存在就是要阻止菁英壟斷政治運作,但為了將民粹主義與其他所有挑戰現任者區隔開來,作者接著提出一個重要的主張:民粹主義者擁有「反多元」特質,他們「假設」有一個「合法人民」的群體(排除那些反對者與移民),他們有一個「最終民意共識」,而這個候選人是真正能代表「真實民意」的人;而那些反對候選人的人,都是「漠視民意」的,只是為了個人的利益。
作者運用世界各國的最新例子,來定義何謂「民粹主義」,方便讀者運用在實際的政治判斷上;他明確地說民粹主義是一種對民主的傷害,但卻是「代議民主永恆的陰影」,他說民粹主義「迫使自由民主的捍衛者更認真思考,代議制度目前的失敗之處是什麼?它應該也要促使他們去解決更一般的道德問題。屬於這個政體的標準是什麼?為什麼多元化真的值得維護?」這些問題,在行至民主深化關鍵期的台灣,尤其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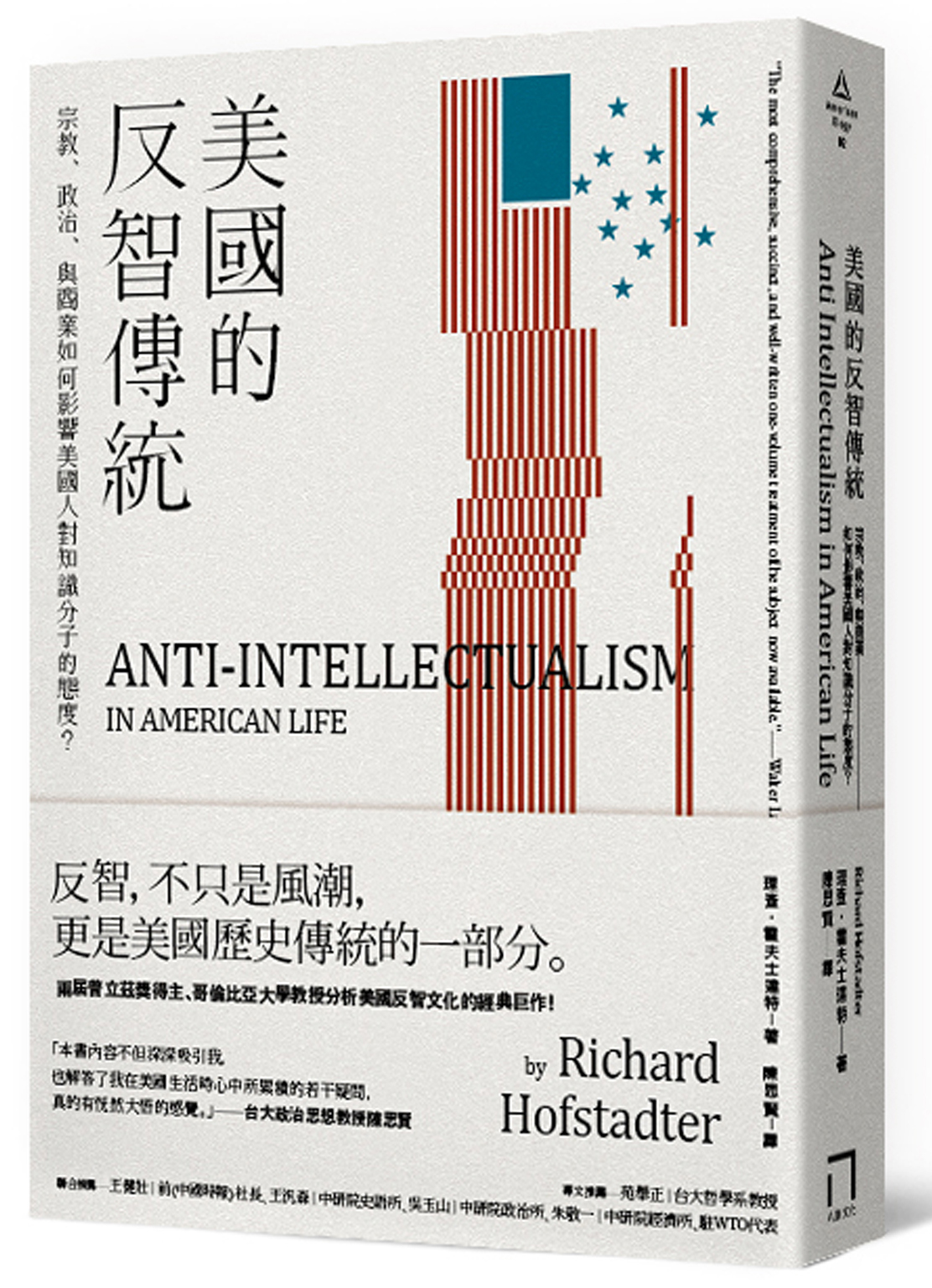
理察‧霍夫士達特
八旗文化,NTD $650,平裝 / 624頁
《美國的反智傳統》
五十年前寫下的川普推背圖?
「在美國的核心地帶,陸續出現了一群內心充滿怨懟的人,他們可能是宗教基本教義主義者、帶著偏見的美國至上論者、外交政策上的封閉主義者與經濟上的保守主義者等,匯集成為一股在現代化下遭逢困境的反對浪潮。」上述的這段話,看起來像是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選民側寫,其實是出自一本半世紀以前的書:《美國的反智傳統》。
55 年前,作者霍夫士達特著書的背景是為了回應麥卡錫主義所造成的白色恐怖:在冷戰對峙的世界局勢下,麥卡錫針對知識分子「抹紅」,指稱他們是共產黨,然而在作者一一爬梳美國歷史之下,這種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乃至於對「務實」的莫名崇拜,根本就是從建國之初即內建在每個美國人心中:美國憲法揭示了「人人平等」的烏托邦,不以身家財產為基準、也不論貴族或販夫走卒、更不拘學識背景。這個國家由最頂尖的思想家與博學家所創建,他們卻相信一般群眾的智慧,將國家託付給全民,背後的淵源即在於,美國是一個由清教徒自行創建的國家,當初他們就是拋下了歐洲的一切,來到大西洋對岸的「應許之地」,胼手胝足地打下這片江山,因此他們重視實踐,對於歐洲知識圈那些抽象概念的討論斥之為「玄想」。
儘管美國有反智傳統,但其實美國人深知他們需要知識來運作國家,只是無法擺脫對知識分子的懷疑與輕視;作者無意責怪反智的選民,也不是要喚起美國人對知識分子的尊敬,他甚至說:「任何熟悉知識分子的人都知道無須對他們存有太多幻想,但是他們身而為人(也會犯錯)這一事實與他們負有發揚智識的功能之間的關係,就像教會裡雖有也會犯錯的神職人員,但不影響教會的神聖一般。」
台灣社會看似非常崇拜智識,但骨子裡卻有和美國相似的反智傾向:總是以負面的「政客」一詞錯稱「政治人物」、對政治的不信任與不理解、不想理解脈絡與歷史、污名化「意識形態」、吹捧「務實」、以市場邏輯看待政治……若說知識分子對社會提升必須肩負責任,那麼全民政治的意義即在於,這樣的責任就在擁有投票權的你我身上。

《朝日新聞》「混沌的深淵」採訪組
暖暖書屋
NTD $450
平裝 / 422頁
《民主是最好的制度嗎?》
什麼才是「最好」的制度?
「明明努力至此,卻仍不順利。」在前言的這句話完全勾勒出現今「民主」的困境。「民主」這個稱霸二十世紀乃至於後冷戰時期的「普世價值」,世界各地發展進程不一,卻在哪裡都出了不少問題。如果我們還相信民主的價值,那麼那個價值會是什麼?是否有比「民主」更好的方法以謀求那個價值?《朝日新聞》「混沌的深淵」採訪組來到五十年沒有投票的日本大分縣姬島村,他們的村長選舉連續十五回以無投票方式當選,但他們的地方治理成績不差,村長說:「現在的政治不是已經變成『為了選舉』的政治了嗎?」沒有選舉,姬島村民還是過得很好。
另外在匈牙利,有政黨提出「給孩子媽媽兩張票」的政策。孩子沒有投票權,卻讓有投票權的大人決定了未來,在現今高齡化又少子化的社會中,年輕人往往只能概括承受,一出生即背負沉重的財務負擔。還有其他考量世代正義的做法:日本有人提出以平均餘命劃分選區,年輕選區可以分配到更多席次,真正反映每票在人一生中的價值。當初倡議「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先賢們,該不會是以為民主制度無法長久到跨越世代、衍生出世代正義的問題吧?
在這個「民主」日趨成熟運作的今日,有時候選舉成為一種技術問題,而失去了初衷。德國綠黨修改《漢堡憲法》,使地方性公投具有法律約束力;然而在真正施行地方性公投時,結果卻推翻了綠黨提出的議案,綠黨官員嘆道:「藉由公投表現出來的是民意嗎?還是某個具備催票能力的團體的意見?」(這是不是也讓人想到這次綁大選的公投項目呢?)
在全球化的世界裡,問題往往是跨國的,但解決問題的國家卻是各自獨立的,而民主施行的範圍也僅限於一國內,造成國家治理的失效。但這樣的混沌,是「民主」造成的嗎?「為了避免讓錯誤的應對方式加深混沌,就必須正確地提出問題。」然而這僅僅只是檢討民主艱辛的第一步。

大衛‧葛林姆
新樂園出版,NTD $380,平裝 / 400頁
《貓狗的逆襲》
如果無法讓英雄先救貓咪,至少要阻止他不當抱貓
在 2018 年的今天,連沒有寵物的人都可琅琅上口「沒有買賣,沒有傷害」或熟知什麼是 TNR,藉由本次選舉我們更感受到毛公民的強大政治影響力!但本書作者揭示的乃是一個長達萬年的歷史過程,貓和狗因為被人類豢養,漸漸在生理或心理上演化出更能與人接近的特質,到現在成為一種介於野生動物與人類之間的物種,而他們的社會地位演變也充分顯示出這樣的兩難。
在 1866 年,僅僅是林肯提出廢止奴隸制度的隔年,美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成立,起心動念是創辦人亨利‧伯格(Henry Bergh)因為看到車夫虐打拉車的馬匹,而他同時也是紐約防止虐待兒童協會的創辦人。從那時開始,寵物的「權利」有了一日千里的進展,其過程正好和解放奴隸、或兒童福利的做法和理念有若合符節之處:例如將寵物從有主人才產生價值的「財產」,提升為不可估量其價值的「家庭成員」;或是以類似兒童的方式,將「飼主」重新定義為「監護人」,若不幸遭遇離婚或分居,寵物的歸屬也成為必須處理的重要事項。時至今日,寵物們也擁有繼承財產的權利,甚至可以聘請律師。
本書除了貓狗以外,也提及為國家效力的軍犬以及具有正當職業的導盲犬、治療寵物等。但不可否認地是,維權人士策略性地主打貓狗權益,雖然大大地奏效,卻多少對運動的初衷有一定程度的扭曲,甚至出現修正路線的「活體財產」與更倒退的「完全禁絕寵物」的主張,與目前主流的「動物人格」路線相互爭輝。
作者本身因為收養了寵物,而開始了一系列的訪談;而他所訪談的這些動物倡議者,不論是主張應該把他們視為公民者,或是主張必須斷絕寵物者,都有自己的寵物,也幾乎都沒有小孩。當作者的太太懷孕時,他才猛然思索到這個問題:對待小孩和寵物,有先後順序嗎?雖然這很快地不再是一個問題,但這也不禁讓我們思索,「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當動物權與其他權利抵觸時,我們該如何取捨?這樣的思考是否也適用於不同群體之間的相處?
我們都生活在一個複雜的社會裡,生活中遭逢的問題與危險也以等比級數激增中;但我們可用的工具卻愈來愈無效,至少「民主」就是如此。無論是「民粹」或是「反智」,其本質都是企求一個簡單、一元的標準答案:「我就是人民」、「其他人都是腐敗的」、「討論是浪費時間的」;然而綜觀歷史,標準答案不存在,單一共識不存在,只要不深究問題所在,單一解答幾乎都會演變成一場浩劫。如何讓「民主」這個不怎麼樣的工具,盡量發揮出最大功效,就要靠我們的思考了(雖然思考仍然很慢就是了)。就像《民主是最好的制度嗎?》所言:「若民意不存在,民主就只會是一個空箱。在空箱裡,應該只有少數人的聲音能夠響亮地迴響吧」;但也請參考《美國的反智傳統》引用杜威的話:「當人類開始思考時,沒有人能保證後果會是怎樣。我們只能知道因此許多事物或制度會瓦解。每一個思想家都在拆解掉這個穩定世界的一部分,沒有人知道毀壞後什麼東西會出來代替。」
祝各位在混沌的深淵中,仍然保有清明的思考,還有,抱好你的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