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車上的春風少年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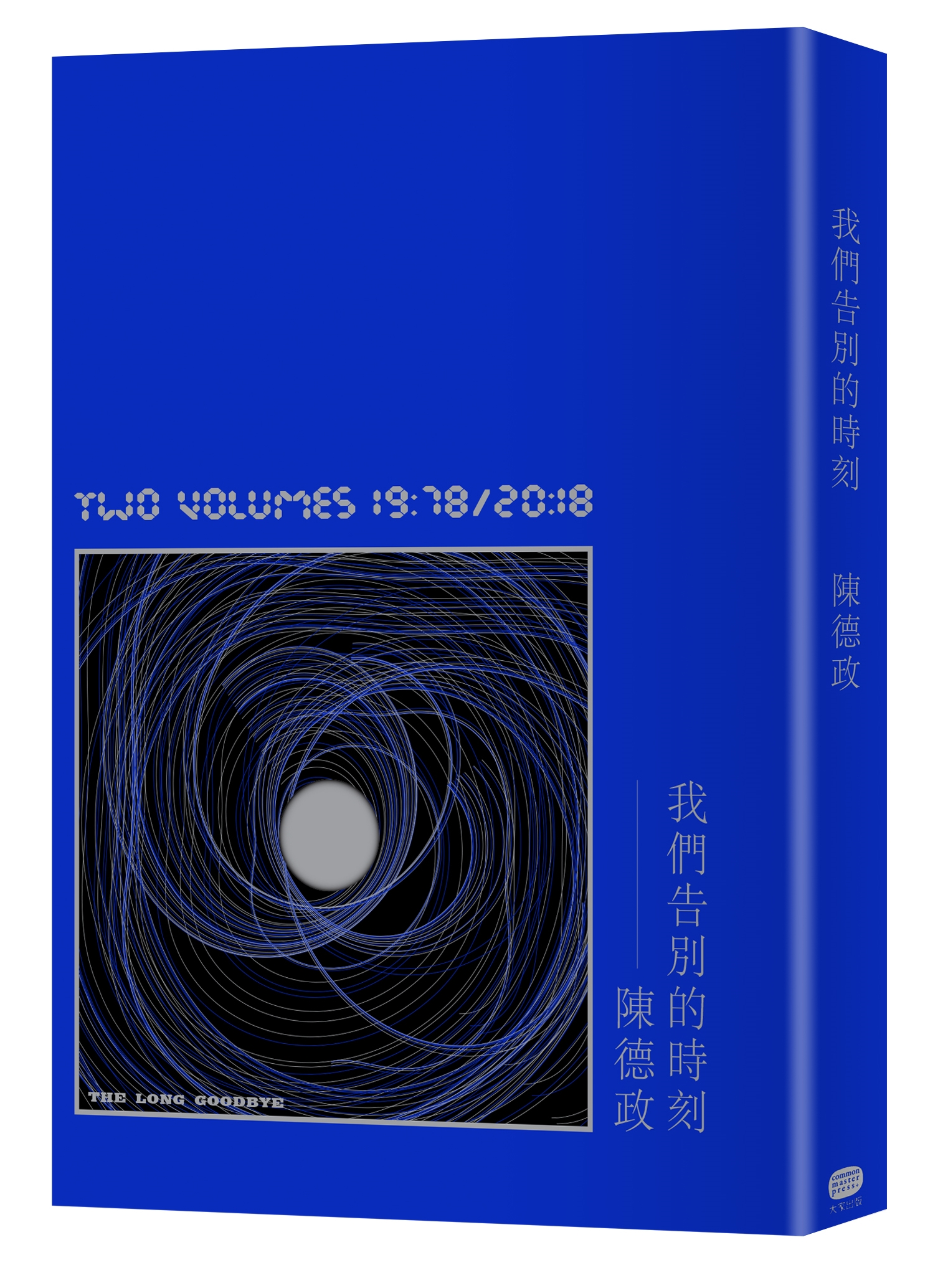
阿水是我在班上最好的朋友。
我們在同一年進了國中,被命運安排到相同的班級,兩個人都是高個子,在教室的最後一排坐隔壁,一起幹些調皮搗蛋的事,幫自己在課堂上存活下來,否則,上課實在太無趣了。
都是一些十三歲的男生喜歡幹的勾當:看漫畫、吃零食、寫惡作劇的信給對面女生班的班花,或是趁老師寫黑板的空檔用橡皮筋彈前排同學的後腦勺。有時膽子再大一點,交換改考卷時會把對方錯的地方塗上正確答案,再用紅筆畫上 100 分。
我們是稱兄道弟的哥兒們,臉上都有擠不破的面皰,留著矬矬的平頭(那保守的年代仍有髮禁呢),我的內心卻隱隱覺察,我們在本質上是很不同的人,有著相異的成長背景和價值觀,那似乎也暗示著,等在兩人前方的會是很不一樣的未來。
他來自社區小學,同學們五湖四海,一個年級塞了好幾十班;我被爸媽遷戶口去讀人數稀少的「實驗國小」,鄰近的師範學院每學期都會派應屆畢業生過來擔任實習老師,而教務處門口掛著一面「請說國語」的告示。進國中前我被保護得很好,台語說不上幾句,彷彿在 1980 年代的教育體制下,台語是某種野蠻的象徵,必須被禁絕,或至少不能擴散。
然後,眾聲喧譁的 90 年代降臨,林強來了!
1990 年底,《向前走》由滾石唱片發行,林強用新派的台語歌顛覆了僵化的教條,他意氣風發地高舉著右手,在台北車站的大廳唱歌、跳舞,身上穿著鬆鬆的高腰牛仔褲,中分的髮線是時代的印痕。
突然間,每一個被隔在首都那座高牆外的年輕人都好想進城打拚,親眼看看那一棟一棟的高樓大廈,因為他們堅信,就像歌中描述的那樣,什麼好康的都在那裡。
專輯發行時我才小六,還得再熬幾年才有資格坐上那班擁擠的北上列車,不過,我的思想卻被那些歌曲先行解放了,教務處門口那面「請說國語」的告示在我的視線中失去了光澤,漸漸變得可疑起來,它所代表的權威性也持續在我心底崩解。
林強讓許多人知道,「沒關係,說台語也是可以的。」甚至是「說台語是酷的!」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凡事並非只能有一種選項。
阿水嚼著一口道地的台語,平常在學校反而不習慣說國語,他聽我台語說得「離離落落」,義不容辭擔任我的台語老師,讓我可以打進同儕的圈子。他先教我聽懂,再教我發音的方式,練習的範本取自 1992 年問世的《春風少年兄》,整張專輯都是我們鮮活的教材。
那是林強的第二張作品,同樣是由真言社製作,發行廠牌則由滾石轉移到日系的波麗佳音,是波麗佳音在台編號 00001 的創業作。當時的青少年人手一卷卡帶,封面上的林強從中分轉換成小瓜呆的髮型,帶起另一波風潮,「我要剪成這樣!」好多青年學子拿著歌詞本到社區的理髮店,指著那張照片請阿姨在動刀時做參考。
同年稍晚,L.A. Boyz 也在波麗佳音出道了,三兄弟的首張專輯《閃》一舉帶動台語嘻哈的熱潮,其實林強開始饒舌的時間點還要更早,《春風少年兄》的第一首歌〈溫柔鄉的槍子〉,他就在俗豔的那卡西電子琴伴奏下,用說書人的口吻道出一則買春的故事。
詞句間暗藏著各種關於性的隱喻,我和阿水聽得似懂非懂,曲末女人欲仙欲死的叫春聲(還添加 echo 效果)更讓發育中的男孩聽得心慌意亂,我們差點沒把磁條從卡帶裡拉出來,檢查是哪一段被魔鬼入侵了。一邊聽,阿水會用下半身對空氣做著前進突刺的動作,他在替自己的槍子暖身。
經過二十多年,那卷卡帶早已不知去向,我到唱片行買回後來重發的 CD,聽出好多當初無法理解的細節,譬如〈我是為你好〉的結構與音色都「非常的 R.E.M. 」,尤其那朝氣蓬勃的口琴聲與林強宛如 R.E.M. 主唱麥可・史戴普上身的「嗚呼」;又譬如,〈玉蘭花〉的間奏原來取樣了百老匯作曲家喬治・蓋希文的〈藍色狂想曲〉。
但最教我想念的,是阿水的身影,如果將每首歌加在一塊兒,好像就能拼出一個完整的他,拼出我們曾經堅定不移的友誼。
國二的帶動唱比賽,他在操場頂著烈日帶領全班大跳〈我的頭殼有問題〉,一邊用手敲響自己的腦袋;午休時他怪腔怪調唱起〈拜六的晚時〉那句「Rock & Roll can touch my heart」,興奮地問我他的英文標不標準;掃地時間我們摸魚打混,他一邊把掃把當成麥克風,鸚鵡般重複著〈花心大少爺〉那句「ㄆㄚˇ小姐」,還和我打賭誰會比較早 ㄆㄚˇ 到馬子。
我們讀的是升學主義掛帥的學校,國三時能力分班,阿水不愛讀書,被流放到校園邊疆的放牛班,他加入幫派,學會逞凶鬥狠,成為進出訓導處的常客。每天午休,訓育組長在玄關用藤條修理人時,會傳來幾聲驚心動魄的慘叫,傳遍了整個校區,我趴在書桌上,睜大了眼睛,好擔心其中會聽到阿水的聲音。
聯考前幾個月他來好班找我,約我放學後到校園角落的樓梯間碰面,我赴約時他正蹲在地上抽菸,我要他讓我哈一口,他斷然拒絕了,「你是好學生,不要碰那個。」他若有所思地起身,靠著樓梯的扶手柔聲唱起了〈查某人〉,開始對我傾訴他和馬子的事情。他說,畢業後想去車廠當黑手,存夠了錢才能快點把她娶回家。
那是我第一次聽阿水談起他的「生涯規劃」,也是第一次在那張總是茫然的臉上,見到那種甜蜜的表情,我覺得阿水的馬子很幸福。
沒和他同班後我的台語退步了,他嘴裡叼著菸,用手摟住我的脖子,逼我和他一起唱完〈查某人〉。我唱得七零八落,他取笑我,我不介意,因為他是我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