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個反覆塗抹的手寫板 評《不安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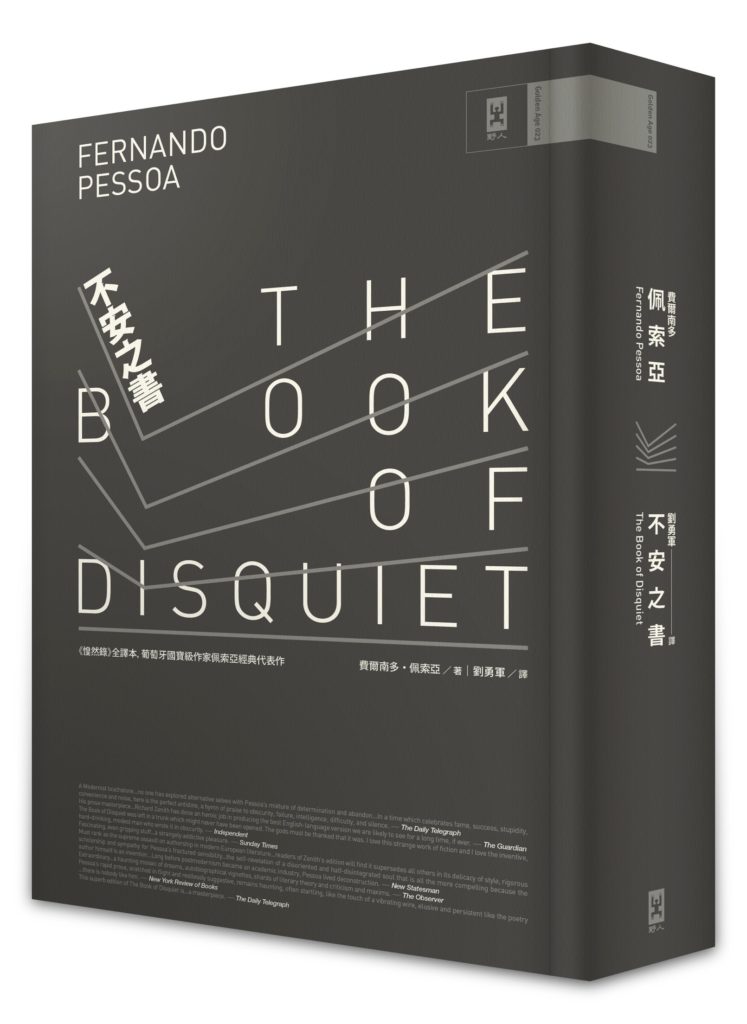
《不安之書:惶然錄》
費爾南多‧佩索亞
野人出版社,NTD $ 650,精裝 / 608 頁
在《不安之書》之前,它有另一個名字《惶然錄》。此書作者佩索亞(Fernando Pessoa,1888-1935)乃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葡萄牙語作家之一,其廣大的文學想像影響超過許多語言、國家與時代的疆界。他與某些作者一樣(譬如卡夫卡與艾蜜莉‧狄金生),生前極為低調單純,甚至乏善可陳,且發表的作品極少,需要後人的整理才成「作品」。相對於先前精選與許多篇名是譯者給予的《惶然錄》,「全譯本」《不安之書》的完整性,值得我們今日的目光留佇,無論之前有無讀過。
進一步說,即使表面上它們是同本書的不同譯本,但我們仍該把它當作另一本書。同時可以當作此書作者佩索亞「異名者」寫作的粗淺隱喻:佩索亞化身為數目眾多的不同名字寫作,這些「異名者」並非一般認知的筆名,而是在他的寫作裡,這些名字確實是一個個不同的書寫主體。每個名字有其身世、性格與寫作傾向,如穿梭紙上的帝國,或是他自己說的,自身是個容納無數角色的舞台,而非扮演者。
一般而論,在日後整理出來的諸多作品集裡,以「索亞雷斯」之名寫下的「日記-隨筆」體裁的《不安之書》,所展露的形象最能貼近佩索亞的內心世界。這指的可能不是透過這本書,能撥開無數的異名者而見證其真實面目,反倒讓我們不無困惑地瞥見「我」的豐饒複雜與矛盾斷裂。在一篇篇的日記裡,他不寫回憶與沈思,多半是當下的感受與頓悟,在此我們看見一個小人物在里斯本,更多時候只在一條小街上游移,毫無大事,僅是一個孤獨者的自言、絮語。所謂的事件,是一個人每次關照自我的一再疏離,我,像是距離最遙遠的物事般,迷人又令人惶恐。
《不安之書》何以迷人?佩索亞呈現給我們的,不是個預設為完整或完成的「作品」,而更像是索亞雷斯之名倉皇寫就的「手稿」。無論何時讀起,皆如掀開塵封已久的古老沈船裡,鐵盒之內竟保存完好的航海日誌,你試著去找出關於某個事件的關鍵、災難的見證,而最終你看到的,不過是個平凡而匆匆來去的短暫生命所留下的潦草書寫;如同沙特的《嘔吐》,虛構起「手稿」並如實呈現給讀者,較早寫出的《不安之書》,實質上更為精確地展現了日後存在主義想表現的「我意識著存在」的不適感:我意識到我、意識到我存在、意識到我在寫,竟如此安然地不安。是以,我寫未必故我在,因為書寫之中,我是空無,是個舞台,是座沒有出口亦無中心的迷宮。
如果我們考量到佩索亞的寫作方法—無處不寫、隨手而寫,任意(或是某種製造偶然的意圖)抓取各種紙張斷片而寫,並任其累積不刻意整裡—便可明白,《不安之書》 能產生如此文學效果(「我」感受到我的存在是如此不安),不僅是組成此書的眾多的、抓住生存之逝之感的私密語言(彷彿牽動神經最細的纖維處),它本身的形式有(更具)決定性的影響。當認識到這種「我」的書寫的本質,正是證成起無盡的朝生暮死的「我」的時刻,這本書的文學價值也就明白許多。它像一本沙之書,但不是對立於完整的「不完整」;一如無盡派生與流變的「我」並非某個完整之我的分裂,而是這才是「我」的本質。
單論「我之書寫」而言,佩索亞是比蒙田更極端的懷疑論者。蒙田細心審視自我,一切,包括自己所見聞、所知與所思,皆可懷疑與否定。蒙田的「Essai(隨筆)」,其實如同字源上的「審度、判斷」,永遠在嘗試與變化,重視過程而非結果的文類,其中關鍵便是那個文間說話的「我」。蒙田不滿足於蘇格拉底的「我只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寧維持在「我知道什麼?」的永恆追問。佩索亞呢?在他那裡,連懷疑本身都不成問題。因為一個「懷疑的我」仍然需要ㄧ個「我」的執念,對佩索亞而言,能依此忖度一切(包括自身)之「我」,早就在寫作中,以無盡蔓生的、「一瞬之我」消解了。蒙田接納「我」之下的各種可能,佩索亞那則是無盡的不同之我,同時以異名(創造無數異名者來書寫)與同名(譬如《不安之書》裡以索雷亞斯之名生產的的各種面貌)存在。相對蒙田的「我知道什麼?」,他說:「我不曾知道什麼,這竟然是真的。」蒙田的準則讓自己維持在此刻思考的懷疑,佩索亞則以書寫當下片刻訝異於過去的虛妄。「我懷疑」已散逸在佩索亞的書寫,我是無,因而可以是任何東西。所以他說:「我是我的同者(我不知道什麼)與異者(我意識到並為此驚訝)。」
我們仍然不能免俗地想問:作為一個一次性的、無比脆弱的、並可能是虛幻的主體「我」,是否如此毫無意義?為此,我們必須仔細再看一次《不安之書》的書寫:整本書在蛛紋般即將破裂「書寫者我」展示的,是無盡的「我的感受」,其強度勝過「我思」。或許,裂紋本身更加昭示著存在的本質。以此而言,他走得比後來的存在主義更遠:真正荒謬的不在於我意識到我與這個世界無意義(如沙特)、或我與世界的疏遠(如卡繆),而是我竟然是我,我的一切竟屬於我。不論是影之分身術(佩索亞每一個異名者本身又能無盡分裂),或是取消夢與現實(夢中能思考,醒時能做夢),在佩索亞手中出現的奇蹟,是一種突然綻放的豐饒,一瞬由孤自個體打開的無限宇宙。伴著惶然,或是不安。從我的抄寫出發,讓自己一再退卻,直到退無可退之處,突然發現背後的無形之牆。所謂界線,那個彷彿無可選擇的僵硬之「我」,已自行取消。從此,再也無所依靠,無比自由。
佩索亞的書寫實踐著韓波終極的「我是他者」,放在二十世紀的文學史來看,這個孤獨的先行者確實走在前方很遠之處。不過《不安之書》整體(重)讀起並未給予前衛之感,而是十分經典。經典,即能渡過時間的考驗,仍帶來感動。這確實是許多偉大作家的共通處,不論是波赫士、惠特曼、甚至塞萬提斯,皆曾以假託他人之名來呈現作品。彷彿關於書寫甚至宇宙最古老的隱喻,世界是個反覆塗抹的手寫板,書寫者只能偶然在其上留下將被抹卻的痕跡。而讀者,在那閱讀的恍惚間,似乎也有幸地,遙遠卻模糊地看見上帝手中,那巨大無形的手寫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