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們一路推向災難的,是貪婪與全球化
如果近幾個月有教會我們任何事,那便是,這世界不僅是平的。它還很脆弱。
而且,是我們親手將世界變成這副模樣的。只消看看四周,在過去二十年裡,無論是生態、地緣政治或金融領域中,人造和自然的緩衝、刻意保留的冗餘到監管與規範,這些在巨大體系面臨壓力時的彈性與保護,都被我們一步步消除。只因對短期效益與成長的痴迷,我們一直不顧後果、或者壓根不假思索地除去這些緩衝。
與此同時,我們也一直以極端的方式行事——違背並打破常識性的政治、金融和地球界線。
且一直以來,我們不斷替全球市場、電信傳播系統、網際網路與跨國旅行添加潤滑劑、減少摩擦力,用科技讓世界從相連、互連,直至相互依存。全球化因此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快、更深、更便宜、更緊密。有多少人知道,從武漢到美國有定期直飛航班?
把以上三種趨勢並置,你會見到一個更容易發生衝擊與極端行為的世界。減緩這些衝擊的緩衝少了許多,傳播影響至全球的網路公司和網路使用者卻多了很多。
顯然,這一點在最近期的全球危機,即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中,被清楚揭示出來。但動盪危機愈發頻繁的趨勢,其實早在過去二十年裡日積月累:九一一事件、2008年金融危機、氣候變遷和 COVID-19。大流行病不再只是生物科學議題,如今還涉及地緣政治、金融與大氣。除非我們開始採取不同行徑、以不同的方式對待大地之母,否則我們必將承擔愈來愈嚴重的後果。
請注意此一模式:在上述每個危機來臨前,我們首先會經歷到可謂「輕度」的心臟病發,警告著我們正走向極端,且保護我們不受災難性失敗波及的緩衝也已被除去。然而,在這一次又一次的案例中,我們都未有認真看待那些警告,以致最終都演變為一場全面的全球性冠心病。
《不可或缺:領導者真正發揮作用的時候》(Indispensable: When Leaders Really Matter,暫譯)作者高塔姆・穆昆達(Gautam Mukunda)解釋:「我們創造全球化的網路,是因為它們能使我們更有效率、更有生產力,並讓我們的生活更為便捷。但當你為了短期效益、或出於純然的貪念,而一步步除去其緩衝、備用容量和過壓保護裝置時,你不僅確保了這些系統更無力抵抗衝擊,甚至確保了我們會將這些衝擊散播到世界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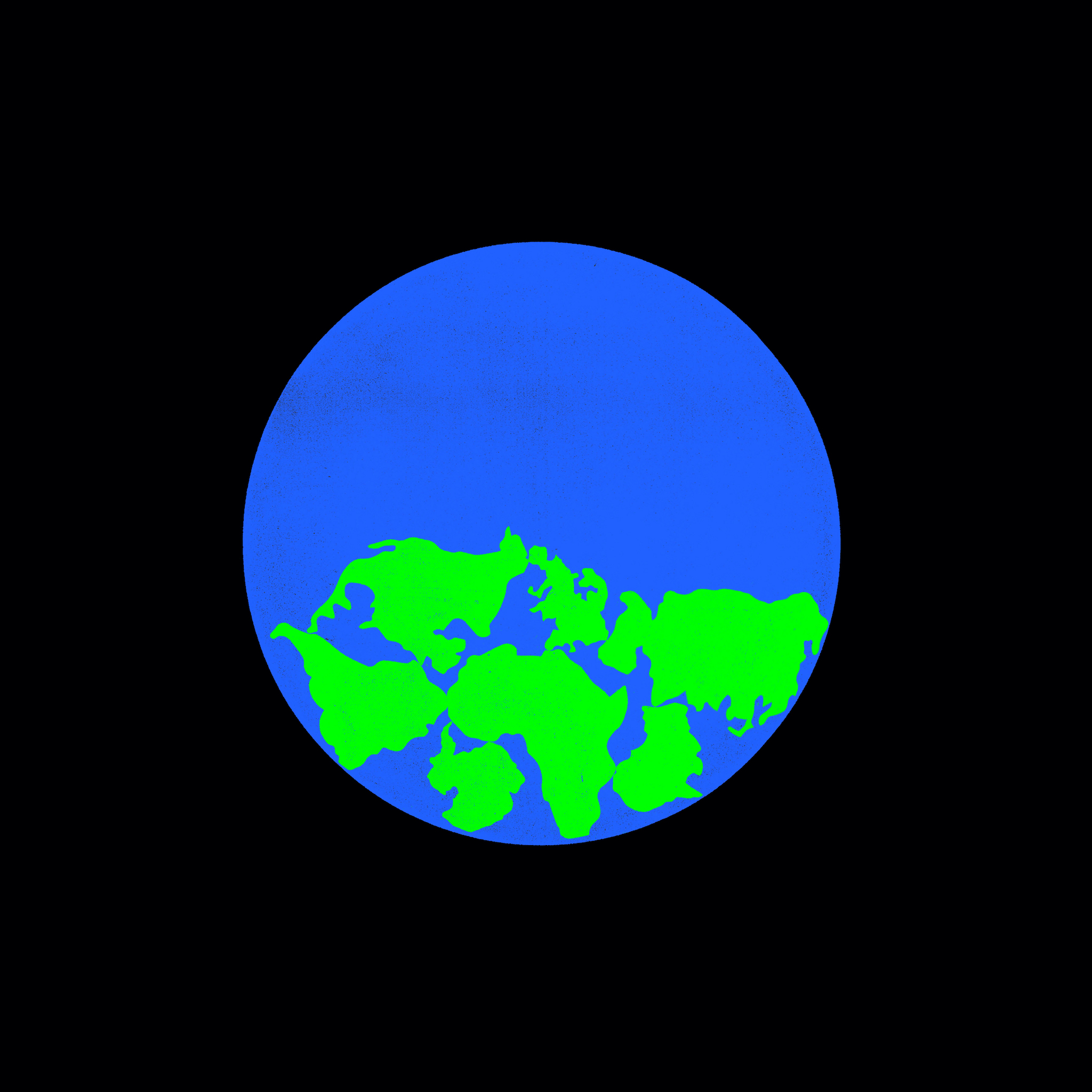
2001年9月11日
讓我們從九一一談起。你可以把蓋達組織與其領導人奧薩瑪・賓拉登(Osama bin Laden)視為1979年後在中東出現的政治病原體。而阿拉伯政治專家馬蒙・范迪(Mamoun Fandy)曾說:「伊斯蘭在1979年弄丟了煞車」,就是在描述伊斯蘭對極端主義的抵抗力嚴重受損。
那一年,伊斯蘭極端分子佔領了麥加禁寺,伊朗的一場伊斯蘭革命將魯霍拉・穆薩維・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推上權力寶座;此後,沙烏地阿拉伯便踉蹌後退。兩起事件引發了什葉派的伊朗與遜尼派的沙烏地阿拉伯相爭,奪取穆斯林世界真正領袖之位。這場鬥爭恰巧碰上了油價飆漲,資助了這兩個基本教義派政權,使它們得以透過全球清真寺和學校宣傳其極端保守的伊斯蘭品牌。
在此過程中,它們也削弱了宗教與政治多元化崛起的任何趨勢,並鞏固了嚴厲的基本教義派與其附帶的暴力。
請記得,穆斯林世界在文化、科學與經濟上最具影響力的中世紀時,摩爾人(註1)所統治的西班牙乃是一個富有的多元文化國度。
無論是在自然界或政治上,多樣化生態系統往往比單一文化更具彈性與適應力。在農業上,單一耕作極易受疾病感染,只要一種病毒或細菌就能摧毀所有作物;政治上,單一文化則極易受病態思想感染。
由於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的競逐,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在1979年後變得愈發單一。而「暴力的伊斯蘭聖戰主義應成為伊斯蘭復興的引擎,清除以美國為首的外國勢力是必要的第一步」這種思想,也得到了更為廣泛的認同。
此種意識形態的病原體經由清真寺、錄音帶和網路擴散開來,傳到巴基斯坦、北非、歐洲、印度和印尼。
1993年2月26日,中午12點18分,預示這種思想甚或會震盪美國的警鐘響起;一輛載滿爆裂物的租賃貨車在曼哈頓世貿中心北塔地下室停車場爆炸。爆炸未能如謀劃者所願摧毀整棟建物,但嚴重破壞了主要結構,並造成6人喪命、多逾1,000人受傷。
這起攻擊的主謀是巴基斯坦人拉姆齊・艾哈邁德・尤瑟夫(Ramzi Ahmed Yousef),他在之後的問訊裡告訴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探員,他唯一的遺憾是這座110層的大樓沒能倒塌、撞向南塔並殺死千萬人。
接下來發生了什麼我們都很清楚:2001年9月11日,直奔雙子星大廈的一記重擊,點燃了一場全球經濟與地緣政治危機。最終,美國政府花費了數億美元,藉由大規模政府監視系統、逃犯引渡、機場的金屬探測器,和興兵入侵中東,替自身接種了對抗暴力伊斯蘭極端主義的疫苗。
美國與其盟友推翻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獨裁者,望能激催生出政治多元性、性別多元性、宗教多元性、教育多元性,作為狂熱主義與威權主義的抗體。不幸的是,我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在如此遙遠的國度做到這件事,我們搞砸了;也證實了該區域的多元抗體之頹弱。
作為一種病毒,蓋達組織在生物學和地緣政治上都發生了變異,並從伊拉克與阿富汗的宿主身上拾取了新元素。結果,暴力伊斯蘭極端主義變得更狠毒,在其基因組的微妙變化下,變成了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伊斯蘭國的出現,以及塔利班內部相應的變化,迫使美國續留在該區控制爆發的「疫情」,卻無法採取更多行動。
金融危機
2008年全球銀行業的危機以相似的方式登場。警鐘由名為「長期資本管理公司」(以下簡稱 LTCM)的病毒所敲響。
LTCM 是投資銀行家約翰・梅里韋瑟(John Meriweather)於1994年創造的一檔避險基金(hedge fund,又稱對沖基金)並召集了數學家、業界資深人士和兩名諾貝爾獎得主共組一支團隊。該基金以數學模型來預測價格、又以無數槓桿(註2)來放大其12.5億美元的創始資本,從而進行規模龐大、利潤豐厚的套利投注。
這一切都很成功,直到它失敗。
《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回顧:「1998年8月,俄羅斯未按期償還債務。三天後,全球股市開始下沉。投資者們開始四處撤資,交易價差(swap spread)糟到不可置信。一切都在垂直掉落。一天內,LTCM 損失了5.53億美元,占其資本的15%,並在一個月內損失了近20億美元。」
避險基金本來就一天到晚賠錢、欠款違約,然後走向滅亡。但 LTCM 和一般的避險基金不同。
這間公司利用來自多家大型國際銀行的鉅額資金作投注,且由於交易不透明,所以交易對手無從得知 LTCM 的整體暴險額。其金額之大,若是它獲准宣布破產並不履行債務,將會替華爾街與海外的數十家投資機構與銀行造成難以計數的損失。
在超過一兆美元面臨風險的狀況下,該公司獲得了美國聯準會(Federal Reserve)的3.65億美元紓困計畫,好讓華爾街的多頭們能對 LTCM「群體免疫」。
該危機得到控制,而教訓也十分清楚:在這個單一參與者從多個不同管道、借了多少資金並不透明的全球銀行體系中,別讓任何人以如此龐大的槓桿,進行如此鉅額、甚至有些極端的投注。
十年後,人們遺忘了這個教訓,於是我們遭遇了2008年的全面性金融災難。
這一次,我們所有人都在賭場裡。四種後來變成「金融病原體」的主要金融工具,造成了2008年的全球危機:次級房貸、可調利率抵押貸款(ARMs)、商用不動產抵押貸款証券(CMBS)、抵押債務證券(CDOs)。
銀行和監管較鬆的金融機構一頭栽進極其魯莽的次級房貸和可調利率抵押貸款,然後和其他單位一起,把這些貸款綑綁成不動產抵押貸款證券。與此同時,信用評等機構又遠遠低估了這些債券的實際風險。
整個體系全依賴著不斷飆漲的房價。因此,當房地產泡沫破裂、許多屋主無法支付房貸時,金融傳染病蔓延感染了全球大量的銀行和保險公司,更別提數以百計的小型家族生意了。
我們已經打破了金融常識的疆界。隨著全球金融系統史無前例地緊密牽連、槓桿化,唯有借助中央銀行的鉅額紓困,才避免了商業銀行倒閉與股市崩盤,不至於引發全面經濟瘟疫和大蕭條。
2010年,我們用美國的《陶德-法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與全球銀行體系採用的《巴塞爾資本協定三》(Basel III)中資本和流動性的新準則,試圖讓銀行體系防範疫情捲土重來。但自此之後(尤其在川普執政時),金融服務企業持續遊說立法機構成員減少這些緩衝,且多半成功,為下一種新興金融病毒提供了誕生的溫床。
這一次,情況可能甚至更危險,因為電腦化交易目前占全球股票交易量的一半以上。這些交易員用演算法和電腦網路,以千分或萬分之一秒的速度處理數據,買賣股票、債券或大宗物資。
哀哉,在貪婪面前,沒有群體免疫這回事。
COVID-19
我覺得我沒有必要在 COVID-19 疫情上花太多篇幅,我只想說:這同樣也曾有過警告信號,它於2002年底在中國南方的廣東省出現:一種由簡稱 SARS 的冠狀病毒引起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網站上如此記載:「在接下來的數月間,此疾病擴散到了北美洲、南美洲、歐洲和亞洲的二十多國」,然後才得到控制。全世界約8,000人確診,其中近800人死亡。
造成 SARS 大流行的病毒宿主是蝙蝠和果子貍。而它會傳染到人類身上,是因為我們不斷地把人口稠密的都會中心向外推展,更深入荒野地區,破壞自然緩衝帶,以單一物種和鋼筋水泥取而代之。
當你透過摧毀一個又一個自然棲地,同時獵補更多野生動物來加速發展時,「物種間的自然平衡,因失去頂端掠食者和其他標誌性物種而崩壞,導致一大票更為廣域的物種調整原有習性,以生活在被人類佔領的棲地中,」非政府組織保護國際(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首席科學家約翰・羅克斯特倫(Johan Rockstrom)向我解釋道。
這些較廣域的物種包括老鼠、蝙蝠、果子狸和一些靈長類動物,而牠們共同帶原著大多數已知的可傳人病毒。接著,當上述動物在中國、中非和越南等地,被當作食物、傳統藥材、靈藥和寵物販售而遭獵捕、誘捕並流入市場時,便危及到了演化過程中不曾碰上這些病毒的人類。
2003年2月,不知道自己已感染 SARS 的廣東醫生劉劍倫訪港,入住香港京華國際酒店(現名九龍維景酒店)911號房,將 SARS 從中國大陸傳入香港。
沒錯,就是「911」號房,不是我編的。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到劉劍倫退房的時候,已將這種致命的病毒直接傳染給了至少8名房客。而這幾人又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再將病毒帶至新加坡、多倫多、河內和香港他處,病毒便在各地繼續散播。據世界衛生組織估算,如今追蹤到的全球7,700多個SARS病例中,有4,000多例都能追溯到劉劍倫在京華國際酒店9樓的住宿。」
但必須注意的是,SARS 疫情在發展成徹頭徹尾的全球大流行之前,便於2003年7月得到控制。很大程度上,這要歸功於即時隔離與多國公共衛生單位的緊密合作。這證實了,跨國合作管治是一個很好的緩衝。
哀哉,那已是過眼雲煙了。國際病毒學分類學會替最新的冠狀病毒取了個恰當的名字:SARS-CoV-2——強調著數字「2」。我們還不確定這個冠狀病毒的源頭為何,但普遍懷疑是在中國武漢透過蝙蝠之類的野生動物傳染給人類的。隨著我們繼續剝奪自然緩衝帶和生物多樣性,類似的跨物種傳染必然會與日俱增。
「生態系統愈是簡化、愈是不多樣,我們愈會成為這些新興危害的目標,尤其是在巨大而不斷擴張的都市地區,缺乏健全生態系統中大量其他物種作為緩衝,」全球野生動物保育組織(Global Wildlife Conservation)主席羅斯・密特麥爾(Russ Mittermeier)解釋道,他同時也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靈長類動物專家。
而我們確切可知的是,在這種新型冠狀病毒於武漢傳到人類身上約半年後,美國已逾10萬人死亡、4,000多萬人失業。
儘管此病毒從歐洲和亞洲傳入美國,但多數美國人或未意識到這種病原體有多麽容易傳入。據美國廣播公司(ABC)研究,去年12月到今年3月的疫情爆發期間,中國有約3,200趟航班飛往美國各大城市。其中,有50趟是從武漢出發的直飛航班,從武漢直飛!有多少美國人聽說過武漢?
飛機、火車和渡輪等全球網絡的廣泛拓展,加上全球合作與管治上太少的緩衝,再加上近80億的全球人口(1918年西班牙流感時全球僅18億人口),在在使這種冠狀病毒得以在轉眼間擴散至全世界。
氣候危機
你得自欺欺人至極,才能不把眼下這一切視為巨大的閃光警告標誌,預告著不僅迫切、還可能是最糟的一個全球災難:氣候變遷。
我不喜歡用「氣候變遷」一詞來描述將至之事。我偏好説「全球怪化」(global weirding),因為天氣變得怪異才是此刻真正在發生的事。極端氣候事件的發生頻率、強度和所造成的損失都在增加,潮濕的地方變得更溼、炎熱的地方變得更熱、乾燥的時節變得更乾、雪下得更厚、颶風颳得更猛。
氣象太複雜了,無法將任何單一事件歸因於氣候變遷,但極端氣象愈發頻繁、愈發代價高昂,特別是在如休士頓和紐奧良這樣擁擠的城市裡,這點無庸置疑。
對我們來說,明智之舉是立即著手保護大自然賦予我們的所有生態緩衝區,如此才能設法處理氣候變遷造成的必然衝擊,並聚焦於如何避免招致失控的後果。
因為,和 COVID-19 等生物性流行病不同,氣候變遷沒有所謂「高峰」。一旦我們砍伐了亞馬遜雨林或融掉了格陵蘭的冰蓋,它就徹底消失了,而我們將不得不忍受任何隨之而來的極端氣候。
舉個小例子:《華盛頓郵報》指出,今年五月,在罕見的大量春雨後,密西根州密蘭德市的埃登維爾水壩(Edenville Dam)潰堤,迫使1萬1,000人撤離家園,「讓一些居民措手不及,但水文學家和土木工程師倒不這麼意外,他們曾警告,氣候變遷和發展造成的增量逕流,正替那些維護不善的水壩帶來更大壓力,其中許多水壩(比如密蘭德市的水壩)是20世紀初為發電而建的。」
但與 COVID-19 疫情不同的是,我們擁有控制氣候變遷和與之共存所需的所有抗體。只要保存並加強那些賦予我們復原力的緩衝區,我們就可以實現群體免疫。那意味著: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保護儲存碳、過濾水源的森林,維持生態系統與物種多樣性,保護能減緩風暴潮的紅樹林。更廣泛而言,協調全球政府制定目標、限制與監管成效的對策。
當我回顧過去的二十年,這四起全球性災難有一處共同點——即它們全是「黑色大象」。這個由環境學家亞當・斯維登(Adam Sweidan)發明的詞彙,是「黑天鵝」和「房間裡的大象」的混合體——前者指不太可能、意想不到,卻實際發生並影響甚巨的事件;後者則是人盡可見、卻無人想去解決的迫切災難。
換句話說,我領著你走過的這趟回顧之旅,或許聽來機械化且不可避免。但並非如此。一切都關乎人類和人類領袖在全球化時代的各個時期所持、或未持的種種選擇和價值觀。
理論而言,全球化的確是不可避免,而我們形塑它的方式則否。
或者,誠如創業投資者暨政治經濟學家尼克・哈諾爾(Nick Hanauer)日前對我所說的:「病原體是不可避免,但演變成全球大流行病並不是。」
我們決定以效率之名移除種種緩衝;我們決定讓資本主義橫行霸道,讓它在我們最需要政府時縮減政府的能力;我們決定濫伐亞馬遜雨林;我們決定入侵原始的生態系統並獵殺野生動物。還有太多的穆斯林神職人員決定,讓過去葬送掉未來,而非讓未來安葬過去。
這就是一切的終極教訓:隨著世界愈發緊密交織,每個人的所作所為,即我們每個人在這個相互依存的世界裡所抱持的價值觀,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所以,「恕道」精神也是如此,它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因為如今,你的所作所為將以更多管道、對更多人、更多地方,造成更長遠的影響,反之亦然。
註1:中世紀歐洲人對居住在北非、伊比利半島、西西里和馬爾他穆斯林的稱呼。
註2:槓桿在金融交易中,指應用衍生工具或是保證金交易,放大每單位本金所涉的資產規模,意欲進而提高投資報酬率。